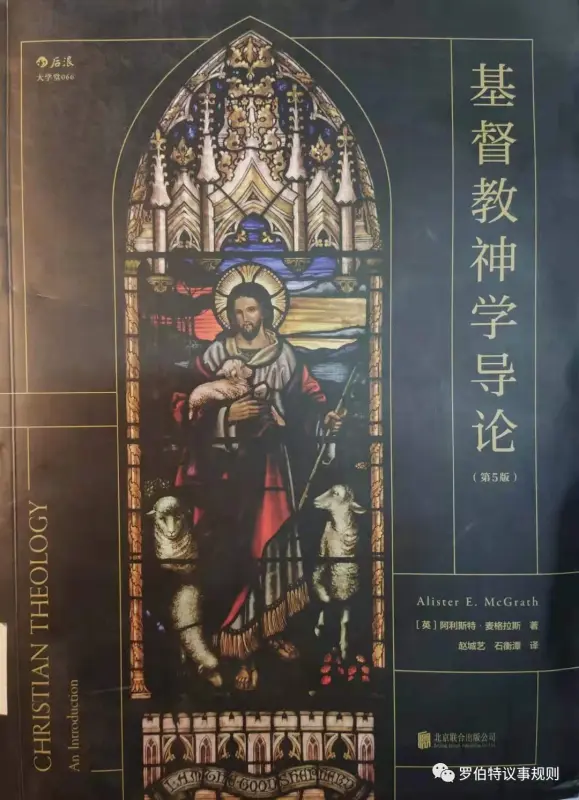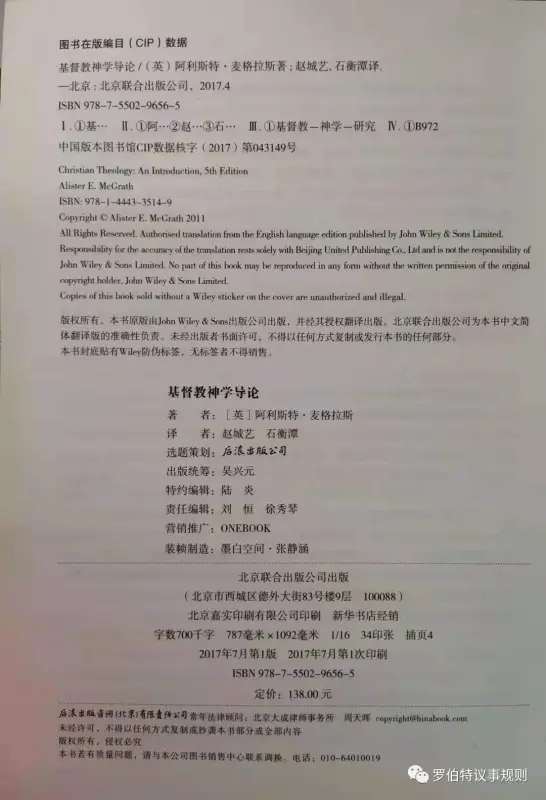zhbglzx
【书摘】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18.2末后的事
《基督教神学导论》
[英]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著
赵城艺 石衡潭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7-07。
…
·正文约7800字
·粗体原文标
·编录:杨原平
…
提要
最后,我们将思考基督教对“末后的事”的教导,这些是基督教的生活和信仰不可或缺的方面,始终是许多神学思辨的主题:1.地狱2.炼狱3.千禧年4.天堂。
第三部 基督教神学
第十八章 末后的事:基督徒的盼望
18.2 末后的事
p509
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思考基督教对“末后的事”的教导。这些是基督教的生活和信仰不可或缺的方面,始终是许多神学思辨的主题,尤其是在流行的讲道和著作中。
p510
1.地 狱
对地狱的兴趣在中世纪达到高潮,可以认为,当时的艺术家或许乐于描述义人看着罪人受火刑和其他酷刑的折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评论过巴黎某些神学家描写地狱的热情,说他们自己显然去过那里。在《神曲》三首诗的第一首中,但丁形象地描绘出中世纪的地狱观。但丁描述,地狱位于地球中心,共有九层,是撒旦的居所。在地狱的门上,但丁注意到这个题词:“凡进入这里的人,都放弃希望!”
地狱的第1层住着没有受洗而死的人和品德高尚的异教徒(这一层相当于此前第442页讲过的“地狱边境” )。但丁宣称,在被钉十字架与复活之间,基督所“降在的阴间(地狱)”就是这一层。这里没有任何痛苦。随着但丁继续深入地狱,他发现。那些人犯的罪越来越重。第二层住满好色者,第三层是饕餮者,第四层是贪婪者,第五层是愤怒者。这几层共同构成“上层地狱”。但丁没有提到地狱的这一部分有火。之后,但丁援用希腊罗马神话,提出冥河将“上层地狱”与“下层地狱”分开。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火。第六层住着异端,第七层是强暴者,第八层是欺诈者(包括几位教宗),第九层是背叛者。
这种静态的中世纪地狱观在当时无疑极具影响力,直到现代时期依然非常重要。乔纳森·爱德华兹讲于1741年7月8日的著名讲章“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清楚讲到了它:
哪怕片刻遭受全能上帝的愤怒就已经够可怕了;但是,你们必须永远承受。这种异常可怕的苦难无穷无尽。……你们将知道,你们必须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亿万年又亿万年中,在这全能而无情的报应中苦苦挣扎。
然而,地狱的观念越来越受到批判,以下几种看法值得注意。
1.基督教宣称,上帝将最终战胜恶,地狱的存在被认为与这种信仰矛盾。这种批判与教父奥利金特别有关。他曾提出万物复原的教义,基础最终在于肯定上帝最后将彻底战胜恶。在现代时期,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这种考量是地狱教义的一大难题:
即使在伟大的永恒未来中,在至善者的至高权威之下,恶还一定战胜善,这似乎非常奇怪。毕竟蒙召的人多,而蒙拣选或得救的人少。
2.《新约》的许多经文提到上帝的怜悯,因此,在许多思想家看来,报复性的公义似乎不符合基督教。特别在19世纪,许多思想家发现难以调和这两种观念:“慈爱的上帝”与“为报复或报应而不断惩罚罪人”。主要的难题是,被定罪的人受苦似乎毫无意义。
虽然可以回答这些反对意见,但是,可以看到普通人和基督教学术界似乎都对地狱的观念失去兴趣。现在,福音派的讲道似乎集中在积极肯定上帝的爱,而不在消极强调抗拒上帝之爱的下场。在福音派中,对这一点的回应是“有条件的永生”(conditional immortality)这个教义,我们现在就来探讨。
p511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福音派内部就一系列末世的问题争辩越来越激烈,焦点是永生的问题。为了回应现代时期对地狱教义的批判,一些福音派学者阐发“有条件的永生”这个教义。菲利普·埃奇库姆·休斯(Philip Edgcumbe Hughes)的《真形象》 (The True Image,1989)便是一个例子。休斯认为,人类被造成时具备永生的潜力:
人是具有肉体和灵体的受造物,永生或不死不是人固有的本性;但是,既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便有这种潜力。因罪而失去的这种潜力已经被基督所恢复与实现。
休斯认为,拯救的本质是实现永生的潜力,条件是对福音的回应。没有回应的人不会进入永生。因此,死后不必再区分善与恶、信与不信。奥古斯丁认为, “在复活之后,最终的普世审判已经完成,那时将有两个国度,界限分明,一个是基督的,一个是魔鬼的。”休斯认为,那时只有一个国度。“当基督充满万有时…怎能想象受造物的一个部分或领域不属于这种完满呢?它的存在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然而,在福音派内,这种“条件主义”或“有条件的永生”遭到强烈反对,詹姆斯·帕克等神学家反对的理由是,它在逻辑上前后不一,也缺乏《圣经》的根据。这场争辩还将继续,可能将在基督教会内蔓延得更广。
2.炼 狱
就理解“末后的事”而言, “炼狱” (purgatory)的问题是新教与天主教的最大差异之一。或许最好将炼狱视为中间阶段,死于恩典中的人最后进入天堂之前有机会洁净自己的罪。在《圣经》中,这种观念没有明确的依据,但是,根据《马加比二书》(2 Maccabees) (新教神学家将这卷书视为次经,所以不具有权威) 12章39至46节,犹大马加比“为死去的人赎罪,使他们能脱离自己的罪”。
这种观念在教父时期得以阐发。亚历山大的克雷苦和奥利金都教导,在去世之前没有时间进行悔改的人将在来生“被火洁净”。为死者祷告的习俗于公元4世纪在东方教会十分普遍,对神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即仪式如何影响神学。有人会问,如果为死者祷告不会改变死者存在的状况,为他们祷告还有什么意义?奥古斯丁也有类似看法,教导必须在进入来生的喜乐之前洁净今生的罪。
到了公元4世纪,为死人祷告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为习俗,但是,大格列高利(约540-604年)可能在两个世纪以后才在著作中明确阐释“炼狱”的观念。(p512)大格列高利于公元593或594年讲解《马太福音》 12章32节,提出罪“在世”可以被赦免的观念。他的解释是,未来有一个时期,在地上没被赦免的罪那时会被赦免。请注意他特别提到“洁净的火” (pugatorius ignis ) ,中世纪对炼狱的大多数描述都提到这个词,它是“炼狱” (purgatory)一词的来源:
p512
至于某些较小的过错,我们必须相信,在最后审判之前,有一种洁净的火,因为真理本人说:“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31)。由此可知,某些过犯在今世可以赦免,有些则在来世可以赦免。
“洁净之火”与“惩罚之火”不同,热亚那的凯瑟琳( Catherine of Genoa, 1447-1510年)在《论炼狱》 (Treatise on Purgatory )中进一步阐发洁净之火的主题,该书大约于1490年写成:
因为炼狱中的灵魂没有罪咎,人和上帝之间没有任何障碍,除了他们的痛苦,痛苦阻碍他们,因此,他们不能通过这个天性达到完美。他们也可以看见,对义的需要是这个天性的阻碍。因此,便出现了烈火,就像地狱之火,只是没有罪咎。上帝不将自己的良善赐给被罚入地狱的人,罪咎使他们的意志邪恶;因此,他们仍有恶的意志,违抗上帝的旨意。
到了 16世纪,改教家否定炼狱的观念。针对它主要有两种批判。第一,它在《圣经》中缺乏实质性依据。第二,它与因信称义教义矛盾,这个教义宣称,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同上帝和好” ,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便不再需要炼狱。在放弃炼狱的观念之后,改教家认为,根本不需要为死者祷告,所以在新教的仪式中删除这种习俗。天主教继续保留炼狱的观念和为死者祷告的习俗。
3.千禧年
初期基督教对天堂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一种相关却不完全相同的观念:千禧年(millennium)或在基督到来与建立全新的宇宙秩序之间,地上复兴的国将持续一千年。这种观念的一个基础是《启示录》的一段经文(启示录 20:2-5),对于初期基督教神学家极具吸引力。公元2世纪的里昂的爱任纽便是很好的例子。对于爱任纽来说,许多考量可以证实世上千禧年的观念,尤其是基督在最后晚餐时的应许:将再与自己的门徒喝新葡萄汁。爱任纽问道:如果他们是没有肉体的灵,这怎么可能呢?既然提到未来喝葡萄汁,肯定说明在最后的审判之前,上帝的国将在地上建立。公元3世纪的德尔图良在著作中对这种观念的阐释可能是最清晰的。
p513
因为我们也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先有地上的国度,在天堂之前——却是在另一种情形中,在复活之后。这将持续一千年,在上帝亲自建立的城中,就是已经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使徒也将它称为“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 (加拉太书4:26)。当宣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 20)时,即“天上的”公民,他肯定指天上的城。……我们肯定,这是上帝建立的城,为要在复活时迎接圣徒,使他们享有一切丰盛的祝福,当然是灵性的祝福,以补偿我们在今世所鄙视或失去的祝福。上帝这样做的确是对的,也确实与他相配,因为他的仆人也应当在他们为他的名受苦的地方欢喜快乐。这便是那个国度的目的,它将持续一千年,圣徒迟早将按照自己的功德复活。当圣徒全部复活时,世界将毁灭,审判的大火会燃起;我们将“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变成天使的本质,“变成(原文为‘穿”)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15: 52—53) ,我们将被接入天国。
对于德尔图良来说,千禧年是这样一个时期:在最终被接入天堂之前,义人曾为信仰所受的苦得到补偿。
然而,公元3世纪,千禧年的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例如,希波里图斯认为,提到一千年的经文不应当按照字面理解,以为是预言将持续一千年的地上国度,而应当是寓意的说法,说明天国的宏伟壮丽。结果,复活的主题逐渐对于教父更加重要。
但是,近年来,千禧年的观念在新教流行的神学和讲道中渐渐重要起来。在以下部分中,我们将概述读者可能遇到的三种主要看法,以及它们的一些代表。
无千禧年主义 如前所述,大多数神学家不认为,千禧年在基督教对于未来的盼望中非常重要。大约公元400年以后的大约1500年间,这种看法是基督教的典型思想。随着基督教国家在西欧和西欧之外稳固建立起来,人们普遍对末世论失去兴趣。尽管费奥雷的约阿基姆等神学家偶尔能激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但是,相对较少的主流神学家详细探讨过这些问题。例如,新教改革时期,对末世论问题的讨论少得惊人。几乎没有主流的新教改教家注释过《启示录》。虽然有过例外,但是,对于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千禧年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然而,随着特别强调千禧年作用的看法兴起,使得上述看法被称为“无千禧年主义” (amillennialism),以区别两种可选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前千禧年主义 这种看法与时代主义有关(却不局限于此),认为所谓的“敌基督者”将在世上出现,(p514)造成七年所谓的“大灾难”。如前所述,这是公元400年以前的初期教会的主要看法。根据对末世的这种解释,上帝在善恶决战(Armageddon)中击败魔鬼,结束地上七年漫长的毁灭、战争和灾难。此后,基督将回到世上统治一千年(千禧年),邪恶的势力被彻底击败。这通常与另一种信仰为伴,即“大灾难之前被提” (pretribulation rapture) ,认为基督徒将在大灾难和基督复临之前从地上被提升天。需要理解的重要一点是,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是十分悲观的世界观,相信世上的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直到上帝终结历史。如果读者想更好地理解这种看法,我建议阅读《末世迷踪》 (Left Behind) ,这是蒂姆·拉哈伊(Tim LaHaye, 1926- )和杰里·詹金斯(Jerry B. Jenkins,1949- )的系列畅销小说,其中反映出前千禧年主义。
p514
后千禧年主义 这种看法于19世纪在美国新教中兴起。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认为,基督将在很长一段公义与和平的时期(不一定是一千年)之后复临,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千禧年。查尔斯·霍奇(1797-1878年)和本杰明·沃菲尔德(1851- 1921年)等普林斯顿学者(主要的新教保守派神学家)认为,通过人类在对抗恶的过程中取得稳步进展,逐渐建立基督教化世界,上帝正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后千禧年论认为,教会在基督复临之前在改造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缔造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 ,教育、艺术、科学和医学都取得巨大进步。前千禧年主义普遍是悲观主义,而后千禧年主义乐观得多。后千禧年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和伤害极大地损害了后千禧年主义的可信性,也加增了前千禧年主义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北美。
4.天堂
基督教的天堂观基本是上帝的同在和能力在末世的实现,以及罪最终的消除。最有帮助的思路是,将它视为拯救教义的圆满成功,罪不再存在,罪的惩罚和势力最终被彻底消灭,上帝与每一个信徒和信仰团契都完全同在。
应当指出,《新约》天堂的比喻带有极强的团体性;例如,天堂被描述为宴席、婚宴或一座城——新耶路撒冷。也可以认为,从个人的角度解释天堂或永生存在不足,因为基督教将上帝理解为三位一体。因此,永生不是映射个人的存在,而是应当被视为与得救的整个团体分享满有爱的上帝的团契。
“天堂”一词在《新约》的保罗书信中经常使用。虽然很自然将天堂视为未来的实体,但是,保罗的思想似乎既包括未来的实体,也包含与时空的物质世界同时共存的灵性领域或国度。因此“天堂”既指信徒未来的家(哥林多后书5: 1-2;腓立比书3:20),也指耶稣基督现在的居所,在最后审判时,他将从那里降临(罗马书10:6;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4:16)。
保罗对天堂最重要的阐释之一,核心是信徒为“天上的国民”这个观念(腓立比书3:20),从某些方面而言,信徒现在便享受到天堂的生活。保罗对天堂的阐释明显有“已经”与“还未”的矛盾,这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天堂在未来才会实现,或天堂是现在无法经历的。
p515
特别是在说希腊语的教会,复活身体的本质是思辨的焦点。当最终从死人中复活时,地上身体的复原,他们在地上仍有人的身体。但是,焦点现在转移到复活,奥利金(约信徒会有怎样的身体?对千禧年的强调不再使人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焦点是信徒在185-254年)很快便成为思考这个问题的主要神学家。
奥利金发现,自己不得不为复活的教义辩护,驳斥两种敌对的教导,在他看来,每一种似乎都歪曲了基督教信仰。一方面,有些神学家认为,复活只是在末日重组人的身体,都是恶的,从而否定从物质的角度对复活的所有理解。对于奥利金来说,复活的身体显包括身体的所有物质的方面和功能。另一方面,批判基督教的诺斯替派认为,所有物质性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反映出他的柏拉图主义前提,最明显的是柏拉图哲学对灵然是纯粹的灵性实体。复活的身体没有适合地上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是能适应天上的灵魂不朽的教导。
按照上帝的命令,地上动物的身体将被灵性身体取代,从而能住在天堂;甚至是较低微的人,受鄙视的人,价值不足挂齿的人,身体的荣耀和价值仍将按照每一个生命和灵魂应得的比例赐下。
然而,奥利金也坚持认为,复活的身体拥有和地上身体一样的“形式”(eidos)。因此,复活包括灵性的改变,却没有失去各自的特性。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奥利金所持的看法似乎将身体与灵魂彻底分开。这种二元论源自希腊哲学,而不是《圣经》。
奥利金后来的批判者认为,奥利金对复活身体的教导的另一个方面,也显露出他的柏拉图主义。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斯丁尼批判奥利金教导复活的身体是球状的。在对话录《蒂迈欧》中,柏拉图认为,球体是完美的形状,因此,奥利金可能把这种信念纳入到自己的教导中。但是,奥利金已知的著作都没有明确提到这种观念。
奥林匹斯的美多狄乌斯(Methodius of Olympus,死于约311年)对奥利金的批判更为猛烈,他在著作中提出修正的看法。美多狄乌斯认为,奥利金不能真说“身体的复活” ,原因非常简单:复活的不是身体,而是某种难以捉摸的“形式”。美多狄乌斯与亚格劳封(Aglaophon)的对话录写于大约公元300年,其中提出另一种看法,仍然强调未来身体复活的真实的物质层面,依据是金属雕像的熔化和重铸的类比。
这好像某位技艺娴熟的艺术家创作一尊贵重的雕像,用金子或其他材料镶铸,(p516)形态优美匀称;后来,这位艺术家突然发现,雕像的外观被心存嫉妒的人毁坏,他不能忍受雕像的美丽,所以决定毁掉它,以满足自己的嫉妒心,从而获得毫无意义的快乐。因此,这位艺术家决定重铸这尊贵重的雕像。现在请注意,最聪明的亚格劳封,他曾在这尊雕像上花费那么多工夫,精心照料,尽心完成,如果他想确保雕像完美无瑕,便必须将它熔掉,还以原貌。……在我看来,上帝的计划似乎与这个人类的例子大同小异。……因此,上帝再次将人类熔化成他的原始材料,所以能重铸他,使他完美无瑕。因此,雕像的熔化相当于人类身体的死亡和分解,重铸材料相当于死后的复活。
p516
希波的奥古斯丁也批判奥利金的看法,他的解释是,保罗所说的复活身体的灵性本质不是纯粹的灵性身体,而是顺服圣灵。
那么,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人在天堂中将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某人在60岁时又去世,当他出现在新耶路撒冷的街上时,他看起来会像60岁吗?如果某人在10岁时去世,他还将是孩子的样子吗?这个问题让神学家颇费笔墨,尤其是在中世纪。到了13世纪末,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共识。每一个人30岁左右都是最完美的,他们复活时将是这时的样子–即使他们从未活到这个年龄。因此,新耶路撒冷将住满有30岁相貌的男男女女,活却没有一丁点瑕疵。既然基督去世时是30岁左右,这应当被视为完美的年龄——所以是在天堂中复活得荣耀之人的年龄。彼得·伦巴德(约1100-1160年)以当时典型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
出生之后便立刻死去的男孩复活时的样子,将是如果他能活到30岁时该有的样子,根本不会受到他身体任何缺陷的妨碍。由此可见,这个出生时非常小的物质复活时变得非常大,因为它在自我繁衍,自我增加。由此可见,即使他还活着,物质也不是来自其他源头,而是自我增加,就像亚当的肋骨,女人是用它造的,也像福音书中大量增加的饼。
基督教后来对复活身体的讨论,试图探讨对这个问题两种看法之间的矛盾,即从物质的角度与从灵性的角度理解复活身体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指出,争辩被普遍视为思辩性的,毫无意义。其他争辩也可以被视为这种争辩,包括天堂中的人是否也有相对的等级或地位。公元5世纪的神学家居比路的狄奥多莱(Theodoret of Cyrrhus)认为,既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约翰福音14: 2) ,天堂中的人在世时的成就必然决定他们在天堂中相对的地位和特权。这种“功德决定地位” (status by merit)的教义在米兰的安布罗斯的著作中仍然存在,在中世纪神学中也有所反映。
p517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教义声名狼藉,一个原因是新教通常不喜欢“功德”的观念。但是,“不同程度的祝福”这个观念在 16世纪末和 17世纪初清教徒的灵修著作中似乎一直存在。因此,威廉·富尔克(William Fulke,1939—1989年)承认天堂中有不同程度的荣耀,但是,他认为,这是上帝对万物满有恩典的安排,而不是因为特别蒙恩的人有任何功德:
正如星的荣耀各有不同,不是因为它们的功德,而是按照上帝创造它们时的恩赐;同样,圣徒的身体也将各有各的荣耀,不是按照它们的功德,而是根据上帝在复活时无偿的恩赐。
在本书的最后,基督教对天堂的盼望有一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荣福直观(beatific vision)。基督徒最终得以完全见到迄今只能片面认识的上帝。完全见到上帝威严的荣面,始终是许多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尤其是在中世纪。但丁的《神曲》这样结尾:诗人终于瞥见上帝,那是“移动太阳和其他星星的爱”。对这种奇妙而荣耀的异象的盼望被视为有力的动力,推动基督教生活持续下去。正如英国诗人约翰·邓恩(1572-1631年)于三百年前所说: “没有人曾见到上帝还能存活。然而,我见到上帝才能存活;当我见到他时,我将永远不死。”
基督教神学永远无法完全捕捉那个上帝的异象。但是,它至少向我们发起一个挑战,要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上帝,使我们对它的主题兴奋不已。它甚至可能激发我们对未来的兴趣——以这个注释结束这部基督教神学主题的基本概论一定非常合适。
研讨问题
1.任选以下一种观念,探讨它在《新约》中的用法:上帝的国、天堂、复活和永生。 在探讨时,使用经文汇编会非常有帮助。
2.概述鲁道夫·布尔特曼或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对复活的解释。(你需要参考第12章的一部分内容回答这个问题。)
3.研究在本章遇到的以下术语:圣灵时代、去神话化、被提、大灾难和两座城。它们各与以下哪位神学家或哪场运动有关?希波的奥古斯丁、鲁道夫·布尔特曼、时代主义和费奥雷的约阿基姆。(请注意:其中两个术语与同一位神学家或同一场运动有关。)
4.为什么今天在许多(而不是全部)基督徒中探讨地狱越来越不流行?
5.人人都会上天堂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参考第17章介绍的一些内容。)
6.基督教盼望是关乎现在,还是关乎未来?
…
著者简介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McGrath)1953年出生,英国北爱尔兰人,获得牛津大学神学、文学和分子生物物理学三个博士学位。享誉世界的基督教神学家、护教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 Andreas Idreosf科学与宗教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前院长,同时兼任剑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神学、系统神学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反对新无神论、反宗教主义,拥护神学批判实在论。著有《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科学与宗教引论》《无神论的黄昏》《道金斯的迷思》《历史神学》《追求真理的激情》《基督教的未来》等。
译者简介
赵城艺,先后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博塞普世神学院(日内瓦大学),现任教于江苏神学院。译著有《基督教神学导论》《基督教教义简史》《基督教史》等。
石衡潭,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第三十届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作有《自由与创造: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导论》《光影中的信望爱》等,译著有《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自由精神哲学》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牛津大学教授基督教神学几十余年的心得之作,简洁而清晰地阐述了有关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知识。书中概述了历代以来基督教伟大传统中的核心主题,向读者展现出基督教神学的丰富思想及其历史渊源,通过分析与思考来让读者理解每种思想的优劣,让读者充分掌握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点与深刻洞见。作为当今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基督教神学教科书,本书选材精当,编排合理,广受世界各地师生欢迎。无论是研习基督教神学,还是了解基督教文化,本书都是必读的入门佳作。
目 录
第一部 划时代的里程碑:历史时期、主题、基督教神学家
导论…003
第一章 教父时期(约100约-700年)…005
第二章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约700-约1500年)…023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期(约1500-约1750年))…045
第四章 现代时期(约1750—现今)…069
第二部 来源与方法
第五章 准备启程:起步的基础…107
第六章 神学的来源…127
第七章 认识上帝:自然与启示…161
第八章 哲学与神学:对话与争辩…183
第三部 基督教神学
第九章 论上帝…211
第十章 论三位一体…253
第十一章 论基督的位格…291
第十二章 信仰与历史:现代的基督论议题325
第十三章论基督的拯救…347
第十四章 论人性、罪与恩典…385
第十五章 论教会…417
第十六章 论圣礼…445
第十七章 基督教与世界宗教…473
第十八章 末后的事:基督徒的盼望…495
神学术语表…519
出版后记…528
===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