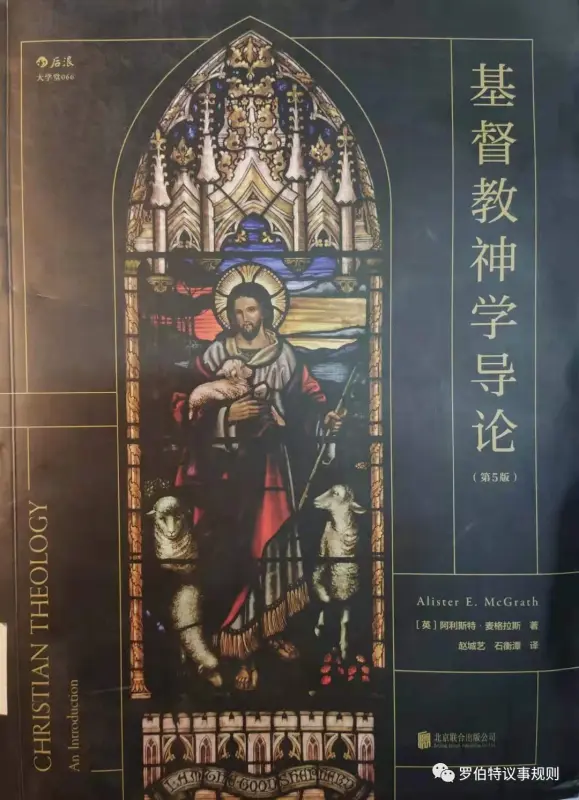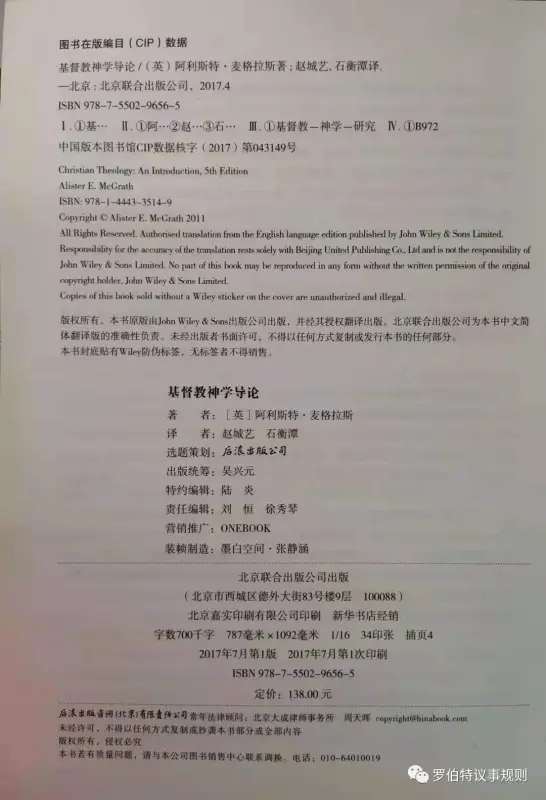zhbglzx
【书摘】麦格拉斯《基督教神学导论》 “论圣礼”16.5 圣餐:真实同在的问题
《基督教神学导论》
[英]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 著
赵城艺 石衡潭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7-07。
…
·正文约6800字
·粗体原文标
·编录:杨原平
…
提要
圣餐的功效是什么?圣餐的饼和酒与普通的饼和酒有什么区别?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对饼和酒说的话,以及在教会的圣餐礼中重复这些话,显然是圣餐的基础,所以非常重要。关于真实同在的三种主要看法:变质说、合质说、纪念说。
第三部 基督教神学
第十六章 论圣礼
16.5 圣餐:真实同在的问题
p460
对于基督教来说,圣礼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从最一开始,圣礼便对基督教的生活和崇拜至关重要。圣餐尤其如此。甚至在《新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最早的基督徒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通过饼和酒纪念他(哥林多前书11: 20-27)。
因此,不可避免且完全合乎情理的是,解释这种做法的意义在神学上受到极大关注。圣餐的功效是什么?圣餐的饼和酒与普通的饼和酒有什么区别?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对饼和酒说的话,以及在教会的圣餐礼中重复这些话,显然是圣餐的基础,所以非常重要。
然而,“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 26: 26)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一定指耶稣在圣餐掰饼时的真实同在——这种观念通常被称为“真实同在观”。这便是我们将在这部分中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本身非常有趣,就自宗教改革以来在基督教内产生的分歧而言,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初期基督教如何理解饼和酒的意义,耶路撒冷的西里尔(约 313—386年)的“教义问答讲稿”是特别重要的见证。这一系列讲稿有 24 篇,教导基督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是西里尔于大约公元350年讲给准备受洗的新信徒的。这个重要的见证让我们了解到公元350年左右耶路撒冷教会中盛行的观念。西里尔显然认为,饼和酒以某种方式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
(耶稣基督)曾在加利利的迦南主动把水变为酒。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信他能把酒变为血呢?……因此,我们应当完全相信,我们是在分享基督的身体和血。因为他的身体以饼的形式被赐给你们,他的血以酒的形式被赐给你们,所以通过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你们可以和他成为一体、一血。
p461
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教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大多数教父相信,证实这种奥秘非常简单。例如,伟大的希腊神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约676-749年)于公元8世纪写道:
那么,你们现在会问,饼如何变成基督的身体,酒和水如何变成基督的血。我要告诉你们。圣灵临到它们,完成任何言语都无法解释、任何思想都无法揣摩的事。……你们只要明白这是圣灵做的,这便够了。
然而,其他神学家更好思辨,导致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争辩。这场争辩于公元9世纪在西方教会中爆发,我们现在就来探讨。
公元9世纪关于真实同在的争辩
公元9世纪,皮卡地(Picardy)的科比(Corbie)修道院燃放了以预定教义和真实同在的本质为内容的绚烂烟火。两位重要的斗士是帕斯卡西乌斯·拉德柏尔图(Paschasius Radbertus, 785-865年)和科比的拉特拉姆斯(Ratramnus of Corbie,死于约868年),他们当时都是法国这座大修道院的修道士。他们各自写了一部同名著作——《论基督的身体与血》 (Concerning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却对真实同在有极为不同的理解。拉德柏尔图的著作完成于公元844年左右,他的观点是,饼和酒实际上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拉特拉姆斯的著作稍晚完成,他捍卫的观点是,它们只是身体和血的象征。著尽管拉德柏尔图没有确切解释普通的饼如何变成基督的身体,但是,他相信,饼真的变成基督的身体,这种改变对基督徒的灵命非常重要:
圣灵当初在童贞女的子宫中,不用任何人的精子,便创造出耶稣基督的肉身;这同一位圣灵,现在每天用他看不见的能力,通过使这个圣礼成圣,创造出基督的身体和血,尽管这不能凭借视觉或味觉从外在理解。
拉特拉姆斯不这样认为,他的论证极为不同。普通的饼与圣饼的区别在于信徒的理解方式。圣饼仍是饼;但是,信徒能理解更深一层的灵性意义,因为它被祝圣过。因此,区别在于信徒,而不在于饼。
通过神父的祝圣,饼成为基督的身体,从外在向人的感觉显现一个样,却从内在向信徒的心灵指明不同的事。从表面看来,饼有同以前一样的形状、颜色和味道;但是,就内在而言,有件非常不同的事更宝贵、更美好,它被彰显出来,因为某件天上与神圣的事——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启示出来。这不是肉体的感官所能察觉、领受或吃下的,而是只能被信徒看见。
p462
第三种看法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富尔达是当时最著名的德国修道院之一,这里的神学家坎迪杜斯(Candidus)认为, “这是我的身体” (马太福音26: 26)指另一种意义的“基督的身体”——基督教会。基督的身体与血的圣礼,目的在于滋养、完善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这是为你们舍的身体。他从芸芸众生中取了这个身体,在受难时掰开,掰开之后又让它从死人中复活。……他从我们这里取走的,他现在已经赐给我们。你们要“吃”,你们要使教会这个身体完全,因此,它可以成为完整、完全的一块饼,它的头是基督。
“记号”与“圣礼”的关系:中世纪的看法
圣礼教义在中世纪的发展产生一些术语,读者可能会发现,理解它们很有帮助。许多神学家发现思考圣礼最简单的方式,即区分“记号”与“它所表示的”;但是,中世纪神学家提出一种三重分类,我们马上就来探讨。
在 12 世纪的神学复兴期间,根据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著作,圣礼的各个方面通过三重区分分类。神学家认为,当思考圣餐时,应当区分圣礼的三个不同方面。经院神学家区分圣礼记号本身(sacramentum tantum)、圣礼所起到的媒介作用(res et sacramentum ) ,以及圣礼的最终效果或“果实” (res et tantum)。在以下部分中,我们将探讨这三种区分,我们将使用你可能在更专业的讨论中遇到的术语。
1.纯圣礼记号(sacramentum或sacramentum tantum ) :这是指圣餐的饼和酒。在这三个观念中,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基本观念是,物质元素(如饼)能表示、引起它本身之外的东西。
2.实体与圣礼(res et sacramentum):某物既是实体,又是记号。以圣餐为例,这是指,经过祝圣的饼和酒应当被理解为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饼和酒仍作为记号而存在;但是,现在又存在额外的实体(拉丁文res,意为“物”)——基督的身体与血,这是以前不存在的。
3·纯实体或圣礼实体(res tantum或res sacramenti ) :这是指圣礼带来的内在与灵性的恩典。以圣餐为例,这应当被理解为领受者参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并从中受益。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这种圣礼实体一方面区别于纯标记(饼和酒),一方面有别于基督的身体和血。问题不是“饼和酒变成什么?”而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为它们的领受者带来什么益处?”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难懂的区分,我们可以思考中世纪举行圣餐的方式,以及饼和
酒的地位在圣餐礼中的变化。以下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对上述三种观念的笼统解释:
p463
1.在祝圣之前,饼和酒只是身体与血的记号,后来才变成身体与血。因此,饼和酒都是纯圣礼记号——纯粹的记号。
2.在祝圣之后,饼和酒的“偶性”或“外观”仍是记号,表示基督的身体与血的真实本质。但是,饼和酒的本质现在已经变成身体与血,身体与血真实地与外在的记号同在。饼和酒现在起到两个作用(实体与圣礼) :第一,就“偶性”或“外观”而言,它们的作用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外在记号;第二,从“本质”或“内在特性”来看,它们真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它们的作用既是圣礼记号,也是圣礼实体。但是,这不是圣礼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圣礼的目的不是使基督的身体与血真实地与圣餐同在,而是传达这所带来的特殊恩典——这便是纯实体,我们现在就来解释。
3.要想理解纯实体的观念,我们需要问一些问题:圣餐要成就什么?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圣餐要取得什么效果?既然饼和酒既是圣礼记号,又是圣礼实体,吃饼喝酒的功效是什么?饼和酒对它们的领受者有什么意义?圣餐的纯实体是信徒与基督的团契,是对未来天堂中荣耀的保证。基督真实地与圣餐同在;但是,他的同在不是目的,而是想要改变信徒。圣餐所要起到的作用或取得的最终功效,是使被视为基督奥秘身体之教会的信徒与作为他们头的基督合一,使信徒彼此合一,让他们安心盼望天堂的荣耀。
关于真实同在的争辩在后来的神学讨论中继续进行,尤其是在中世纪。这个问题到了宗教改革时特别有争议,今天在基督教中仍是争论的焦点。在以下部分中,我们将概述现代基督教的三种主要看法,说明它们的历史发展。
变质说
我们已经讲过,帕斯卡西乌斯·拉德柏尔图坚持认为,饼和酒因祝圣而变成基督的身体与血,尽管他难以用概念解释这种改变。变质教义是对这种看法的巩固与发展。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正式规定这个教义,此次会议可能是天主教16世纪特伦托会议之前规模最大的会议。尽管此次会议没有正式进一步讨论变质的过程,但是,它明确阐述了变质的基本特征。
信徒的普世教会只有一个,没有人能在这个教会之外得救。在这个教会里,耶稣基督既是祭司,也是祭物,他的身体与血真实地包含在饼和酒的种类中,凭借上帝的能力,饼变质为身体(transsubstantis pane in corpus) ,酒变质为血。
在这段文字的讨论中,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用语——特别提到“本质”(内在特性)和“种类” (外观)。(p464)但是,后来到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为更牢固的基础,来说明变质教义的原理。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对“本质”与“偶性”的区分,来解释饼和酒被祝圣时所发生的事。某物的本质是它的本质属性,而它的偶性是它的外观(它的颜色、形状和气味等)。变质论肯定,饼和酒的偶性(它们的外观、味道和气味等)在祝圣时保持不变,而它们的本质从饼和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血。阿奎那坚持认为,饼和酒的本质在祝圣后改变;它们的外观保持不变,但是,它们原来饼和酒的特性消失了。
p464
到了宗教改革时,这种看法遭到新教神学家的猛烈批判,认为这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引进基督教神学。尽管反对阿奎那对变质观的阐释,但是,路德自己的看法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更接近变质论。他对变质教义的主要批评是,这个教义取决于使用异教哲学范畴(即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和“偶性”的观念)。我们很快便会看到,路德自己的看法——被普遍(不是被他自己)称为“合质说” (consubstantiation),认为基督的身体和血的确同饼和酒在一起,或在饼和酒下面。其他新教神学家对这种观念的批判也较为猛烈,尤其是胡尔德里希·茨温利。
直到1551年的特伦托会议,在“论至圣的圣餐礼教令” (Decree on the Most Holy Sacrament of the Eucharist)中,天主教才最终提出明确的立场。在此之前,特伦托会议只是批判改教家,却没有阐释条理清晰的可选立场。现在,这个缺陷已被弥补。“论至圣的圣餐礼教令”开篇便有力地肯定基督真正的本质性同在: “饼和酒被祝圣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这些物体的外观真正、实际、本质性地包含在圣餐这个庄严的圣礼中。”特伦托会议极力捍卫“变质教义”和“变质”一词。“通过祝圣饼和酒,为整个本质带来变化,饼的本质完全变成基督的身体,酒的本质完全变成基督的血。神圣的大公教会将这种改变正确、恰当地称为变质。”
遵照特伦托会议的教令,变质观被视为天主教对真实同在的权威立场,在天主教内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严肃地辩论。这个教义也有难点,特别是自然暴露出它背后极为反直觉的观念。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 年)为变质教义进行过最有趣的辩护之一。在1645年的一封信中,笛卡尔提出,人的消化系统是变质的天然类比。他认为,人的身体是变质过程的有机体模式。自然的消化过程不就是饼变成人的身体吗?根本不需要借助神迹。如果圣餐的变质真需要神迹,也只不过是不需要人体的器官功能为媒介,饼便同化为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有趣的看法,却不受当时教会当局的欢迎。
意义变换与目的变换
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内神学发酵的一个年代,爱德华·谢列比克斯等天主教神学家对变质观进行批判研究。变质观的护教合理性越来越令人担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两种重新理解变质观的方法形成。在这两种方法的倡导者看来,每一种都保留以前变质教义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回应当时形而上的怀疑主义。
p465
目的变换(transfinalization)的观念指,祝圣改变饼和酒的目的或目标。相关观念意义变换(transignification)指,祝圣主要与饼和酒的意义改变有关。这两种观念都避免提到饼和酒的内在特性发生神秘的变化——这种观念在当时怀疑主义气息越来越浓的文化中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目的变换表示,饼和酒的目的发生功能性改变(例如,供养灵性的目的取代供养身体的目的)。意义变换意味着,饼和酒所表示或指明的对象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从表示食物变成表示基督)。这两种观念都基于一个假设,即饼和酒的特性不能孤立于它们的情境或使用。
“意义变换”和“目的变换”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尤其是被一群比利时天主教神学家,他们发现,自己对“变质”这一传统术语感到不安。在重要的研究著作《圣餐》 (The Eucharist, 1968年)中,爱德华·谢列比克斯认为,变质观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这给许多现代人制造出难题。他认为,需要新的看法,它应当保留特伦托会议的基本神学见解,同时不用过时与易受批判的哲学体系说明这些见解。
谢列比克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天主教中,越来越反对对圣餐进行本体论或“物理学的”解释,这与“重新发现圣礼为象征性活动”有关,即意识到“圣礼首先是像记号这样的象征性行为或活动”。谢列比克斯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神学家约瑟夫·德·巴乔基(Joseph de Baciocchi)为这种思维方式指明新的方向,用“功能变换” (transfunctionalism)、”目的变换”和“意义变换”解释他心中的看法。在说明皮特·斯洪嫩贝尔赫(Piet Schoonenberg)和卢凯西乌·施密茨(Luchesius Smits)等神学家对这种思维方式的贡献之后,谢列比克斯阐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基督将自己作为恩赐,但是,这终究不是赐给饼和酒,而是赐给信徒。真实同在的目的是为了信徒,但是,它是以饼和酒的恩赐为媒介,并在其中实现。换句话说,赐下自己的主通过圣礼而同在。在这种纪念性的一餐中,饼和酒成为重新确立意义的对象,这不是人确立的,而是教会永生的主,通过教会,它们成为将自己赐给我们的基督真实同在的记号。
谢列比克斯的要点是,对圣餐的饼和酒的意义的解释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人强行做出的;解释是教会做出的,这是基督已经授权教会去做的。
对于谢列比克斯来说,根本不需要援用的观念是,饼和酒的本质发生物理变化。基督的目的不是改变圣餐的饼和酒的形而上学,而是确保它们说明基督在作为信徒团契的教会中继续同在。
p466
某物可以在本质上改变,而它的物理或生物结构却没有变化。例如,按照与人的关系来看,饼有了完全不同于它对物理学家或形而上学家所具有的意义。饼仍是物理学上的饼,但是,它被纳入纯生物学以外的意义范畴。因此,饼的确不是原来的饼,因为它与人的确定关系在决定我们所谈论的实体时发挥了作用。
天主教对这些进展的正式回应是,只要它们符合传统的变质论,便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饼和酒的确以上述额外教导所肯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饼和酒的目的和意义也必然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庇护六世(Pius VI)在通谕《信仰的奥秘》 (Mysterium fidei, 1965 )中是这样说的:
由于变质,饼和酒的种类无疑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结局,因为它们不再是普通的饼和酒,而是某种神圣之物的记号和灵性之血的记号。但是,它们有了这种新意义,这个新结局,正是因为它们包含一种新“实体”。……因为现已在上述种类之下的(即饼和酒现在的新本质),不是以前在那儿的,而是完全不同的……即基督的身体和血。
合质说
马丁·路德特别倡导合质说,这种看法坚持认为,饼和基督的身体是同时存在的。本质根本没有改变;饼和基督身体的本质是同时存在的。在路德看来,变质教义似乎是谬论,是将奥秘理性化的尝试。
对于路德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基督在圣餐时真正同在——不是某种他如何同在的特殊理论。他借用奥利金的意象说明这一点:如果铁被放进火里加热,它会发热,在发热的铁中,铁和热都是存在的。对于路德来说,他更喜欢用日常生活的这种简单类比,说明基督在圣餐中同在的奥秘,而不是用某种微妙玄奥的形而上学将它理性化。在路德看来,我们要相信的,不是具体的变质教义,而只是基督在圣餐时真实的同在。他认为,这个事实远比任何随后关于它真实性的理论或解释更重要。
真正的缺席:纪念说
对“真实同在”最不形而上学的理解,是瑞士新教改教家胡尔德里希·茨温利特别倡导的。(p467)对于茨温利来说,圣餐〔他更喜欢将其称为“纪念礼” (Remembrance〕)是“纪念基督的受苦,而不是献祭”。由于我们以下将探讨的原因,茨温利坚持认为,“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不能按字面理解,从而排除所有圣餐中“基督真实同在”的观念。好像人要离家远行,他可能将戒指交给妻子,以纪念他,直到他回来;同样,基督留给自己的教会一个纪念品,来纪念他,直到他在荣耀中再来的那一天。
p467
然而,“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 26:26)是什么意思?天主教以此作为传统真实同在观的基础,路德也抓住这句话,为他自己的真实同在观辩护。茨温利认为, “在《圣经》无数的经文中,‘是’的意思是‘表示’。”因此,必须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基督在《马太福音》26章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也可以从隐喻或比喻的角度理解。我们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这个语境中,“是”这个字不能按字面解释。因此,它必须从隐喻或比喻的角度理解。在“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中,“这”指饼,“身体”指将为我们而死的身体。因此,“是”这个字不能按字面解释,因为饼不是身体。
因此,茨温利阐发“意义变换”的理论,饼和酒改变它们的意义,因为它们被用在圣餐礼中。改变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在于崇拜者如何看待饼和酒,而不在于它们的实际特性。因此,饼和酒是基督不在时对他的提醒,是教会盼望的核心,即他的主有一天会再来。基督在圣餐中的同在根本不存在形而上学的难题,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所要讨论的同在。
…
著者简介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E.McGrath)1953年出生,英国北爱尔兰人,获得牛津大学神学、文学和分子生物物理学三个博士学位。享誉世界的基督教神学家、护教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 Andreas Idreosf科学与宗教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前院长,同时兼任剑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神学、系统神学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反对新无神论、反宗教主义,拥护神学批判实在论。著有《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科学与宗教引论》《无神论的黄昏》《道金斯的迷思》《历史神学》《追求真理的激情》《基督教的未来》等。
译者简介
赵城艺,先后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博塞普世神学院(日内瓦大学),现任教于江苏神学院。译著有《基督教神学导论》《基督教教义简史》《基督教史》等。
石衡潭,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第三十届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著作有《自由与创造: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导论》《光影中的信望爱》等,译著有《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自由精神哲学》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牛津大学教授基督教神学几十余年的心得之作,简洁而清晰地阐述了有关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知识。书中概述了历代以来基督教伟大传统中的核心主题,向读者展现出基督教神学的丰富思想及其历史渊源,通过分析与思考来让读者理解每种思想的优劣,让读者充分掌握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点与深刻洞见。作为当今国际上最受欢迎的基督教神学教科书,本书选材精当,编排合理,广受世界各地师生欢迎。无论是研习基督教神学,还是了解基督教文化,本书都是必读的入门佳作。
目 录
第一部 划时代的里程碑:历史时期、主题、基督教神学家
导论…003
第一章 教父时期(约100约-700年)…005
第二章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约700-约1500年)…023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期(约1500-约1750年))…045
第四章 现代时期(约1750—现今)…069
第二部 来源与方法
第五章 准备启程:起步的基础…107
第六章 神学的来源…127
第七章 认识上帝:自然与启示…161
第八章 哲学与神学:对话与争辩…183
第三部 基督教神学
第九章 论上帝…211
第十章 论三位一体…253
第十一章 论基督的位格…291
第十二章 信仰与历史:现代的基督论议题325
第十三章论基督的拯救…347
第十四章 论人性、罪与恩典…385
第十五章 论教会…417
第十六章 论圣礼…445
第十七章 基督教与世界宗教…473
第十八章 末后的事:基督徒的盼望…495
神学术语表…519
出版后记…528
===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