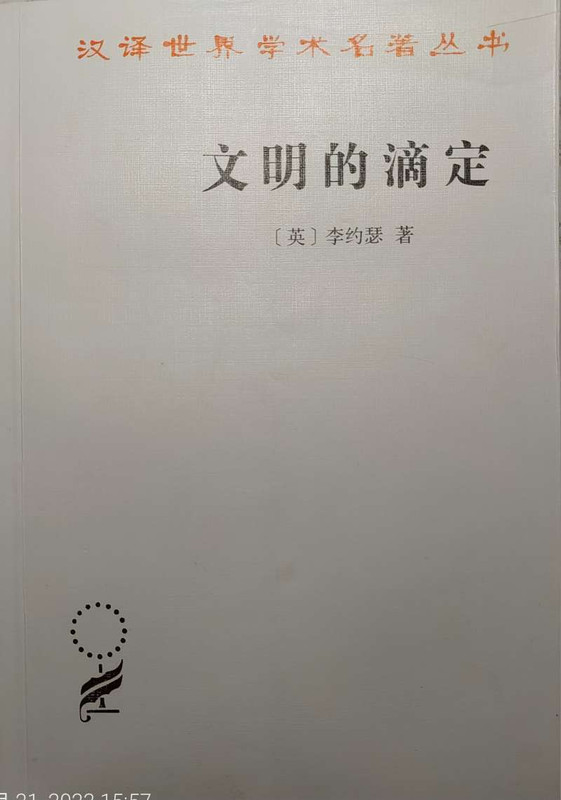zhbglzx
【书摘】李约瑟《文明的滴定》8.人法与自然法则
《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英〕李约瑟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2020-8。
——
·正文约18600字;
·编录:杨原平
——
8.人法与自然法则①
p280
西方文明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无疑是,正如尘世的君主颁布了实在法(positive law)让人们遵守,天界至高的理性造物主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让矿物、晶体、动植物和星辰遵守。我们知道,这种观念与现代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说,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观念,是否是现代科学只在欧洲兴起的原因之一呢?换句话说,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吗?
如果我们看一些讨论科学史的佳作,并且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即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Laws of Nature)一词在欧洲史或伊斯兰教史上最早是何时开始使用的,我们将很难找到回答。当然,这个词在18世纪非常流行,下面这首写于1796年的牛顿式的赞美诗,大多数欧洲人都耳熟能详:
赞美上帝,天言是宣,
大千世界,奉行其言;
自然诸法,永行不断,
天主所制,以统物万。
——
①1951年在伦敦贝德福德学院所做的霍布豪斯(Hobhouse)讲座。原载 Journ.History of Ideas, 1951, 12,3, 194;修订后作为 1961年在哈特菲尔德(Hatfield)技术学院所做的讲座,重印于 Mukerji Presentation Volume (Delhi, 1967)。
p281
然而,本土传统的中国古典学者却写不出这种言辞,为什么呢?
立法者的意志可以体现在他所颁布的法令中。这些法令不仅包括以远古民俗为根据的法令,也包括他认为有利于国家更大福社(或统治阶层更大权力)的法令,后者可能并不以风俗习惯或道德规范为根据。这种“实在”法带有世间统治者发号施令的性质,服从是义务,违法则会受到明确规定的制裁。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它无疑以“法”为代表。而以伦理(例如人通常不会也不该弑其父母)或古代禁忌(如乱伦)为基础的社会习俗则以“礼”来表示,不过“礼”还包含各种仪式或祭典。
我们又知道罗马法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市民法(jus civile)或实在法,即后世所说的成文法(lex lega-le);另一方面则是万民法(jus gentium),多少等同于自然法。在不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则可认为万民法是跟从自然法(jus naturale)而来的。罗马法将万民法与自然法等同起来,尽管这样并不十分稳妥,因为(1)一些习俗对于自然理性来说肯定不是自明的;(2)一些规则(例如奴隶制度不可取)值得全人类认可,但事实上并没有。这种“自然法”源于越来越多的商人和外国人在罗马定居,他们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不必遵守罗马法,而且也愿意受他们自己的法律裁判。面对这种情况,罗马法学家最多也只能从一切已知的民族惯例中取一个最低的共同标准,努力把最多的人认为最接近正义的法律编纂起来。这便是自然法观念的起源。
p282
因此,把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自然正确的法加以平均,便是自然法。正如亨利·梅恩(Henry Maine)所说:“后来,作为市民法之卑微附属品的万民法开始被视为一切法律都应尽可能遵守的一大典范,尽管该典范尚不完善。”这一区分也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把实在法称为dikalov vouurov,而把自然法称为 dikaovovoóv。他说:
政治上的正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约定的。当正义规则在世界各地都同样有效而不依赖于我们是否接受时,它就是自然的;当正义规则起初可以任意制定时,它就是约定的(但一经制定,便不再随意)。比如规定每个囚犯的赎金为一个迈纳(mina),或者祭祀时只能用一只山羊而不用两只绵羊等。……有人认为一切正义规则都仅仅是约定,因为正义规则会变,而自然是不变的,在各处都同样有效,就像火在希腊和在波斯都会烧起来一样。但说正义规则会变也并非绝对正确,毋宁说是有条件限制的。……但尽管如此,的确存在着自然正义和不被自然规定的正义,很容易看出哪些正义规则是自然的(尽管不是绝对的),哪些正义规则不是自然的,而是法定和约定的。这两种规则都是可变的。
这段话非常有趣,因为它指出,与数量有关而与伦理无关的事情只能用实在法来处理,而且几乎谈到了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几乎不存在万民法这样的东西,因为中国文明的“孤立”使得无法从其他部族(gentes)的活动中推演出一部实用的万民法。但中国确实有一种自然法,那就是圣王和民众所一贯接受的那套习俗,即儒家所说的礼。
p283
认为有一位天界立法者为非人的自然现象“立法”,这种观念几乎毫无疑问来自巴比伦人。雅斯特罗(Jastrow)曾经翻译了后期巴比伦创世诗第七号泥板上的文字,其中把太阳神马尔杜克(Marduk)描绘成众星立法者(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着汉谟拉比统一巴比伦和中央集权化,马尔杜克的地位变得极为重要)。太阳神“规定了法让安努(Anu)、恩利尔(Enlil)和埃阿(Ea)等星神去遵守,并且固定了它们的范围”。他通过“号令和敕命把众星保持在各自的轨道上”。
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谈了很多必然性,但没怎么谈自然中的法。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00年)说:“太阳不会逾越其限度,否则(正义女神)狄刻(Dike)的守护神厄里倪厄斯(Erinyes)就会发现它。”这里的规律性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但因为提到了制裁,所以法的观念是存在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560年)也谈到几种自然力在“相互报复和惩罚”。但古希腊诗人所设想的立法者宙斯只是给诸神和人立法,而不是给自然过程立法,因为宙斯本身其实并不是造物主。然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介于墨子和孟子之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了“法”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信任眼睛看到的东西,那么整个世界、神圣的事物还有我们所谓的四季,似乎都受到了法和秩序的控制。”
然而,亚里士多德从未使用过法的隐喻,尽管我们曾经提到,他偶尔非常接近于这样做。柏拉图只在《蒂迈欧篇》中使用过一次,(p284)他说当一个人生病时,他的血液会吸收食物中“违反自然法”的成分。但认为整个世界都受法的支配,这种观念似乎是斯多亚派特有的。这个学派中的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宙斯只不过是普遍的法而已,例如芝诺(Zeno,约公元前320年)、克里安提斯(Cleanthes,约公元前240年)、克吕西普(Chrys-ippus,卒于公元前206年)、第欧根尼(Diogenes,卒于公元前150年)都是这样认为的。这种更为明确的新观念很可能源于巴比伦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公元前300年左右,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占星学家和星官开始遍布于地中海世界。贝罗索斯(Berossus)是其中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是迦勒底人,公元前280年定居于希腊的科斯岛(Cos)。齐尔塞尔向来留心那些伴随着的社会现象,他指出,最早的巴比伦自然法观念产生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东方君主制社会,因此在君主制兴起的斯多亚时代,把宇宙看成一个由神圣的逻各斯统治着的大帝国是很自然的。
p284
众所周知,既然斯多亚派对罗马有巨大影响,那么这些宽泛的观念不可避免会影响所有人共有的(无论他们的文化和当地习俗是什么)自然法观念的发展。当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一前43年)反思了这一点,他说:“芝诺相信自然法是神圣的,其力量既可以使人做正确的事情,也可以禁止人做相反的事情。”还说:“宇宙服从于神,海洋和陆地服从于宇宙,人生则服从于最高的法。”
奇怪的是,我们看到奥维德(Ovid,公元前45年一公元17年)的著作最清楚地表述了法在非人世界之中的存在。他毫不犹豫地用“法”这个词来描述天界运动。谈到毕达哥拉斯的教诲时,他说:
p285
in medium discenda dabat, coetusque silentum
dictaque mirantum magni primordia mundi
et rerum causas,et quid natura docebat,
quid dues,unde nives,quae fulminis esset origo,
Juppiter an vendti discussa nube tonarent,
quid quateret terras,qua sidera lege mearent,
et quodcumque latet…
大多数译者都未能正确处理这段引人注目的文字。德莱顿(Dryden)将其译成:
是什么震撼了坚定的大地,从而开始了
行星围绕光辉灿烂的太阳舞蹈……
金(King)则径直将这段话略去不译。在另一处,奥维德曾在抱怨朋友不忠时说,让太阳往回走,河水流上山,“万物逆着自然法而行”(naturae praepostera legibus ibunt)是很可怕的。
可以更加确定的是,另一条有贡献的思想线索来自希伯来人(或是由希伯来人传播的巴比伦思想线索)。正如辛格(Singer)等人所指出的,我们时常会碰到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超越的神制定了一套法,涵盖了人和自然其他部分的活动。事实上,神圣立法者正是犹太教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希伯来经典中的这些观念对于基督教时代一切西方思想的影响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主为沧海定出界限,水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不仅如此,在《诺亚后裔七诫》中,犹太人又发展出一种适用于所有人、与罗马法中的万民法有些类似的自然法。
p286
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自然继承了希伯来人的神圣立法者观念。我们不难在基督纪元以来的最初几个世纪找到蕴含着自然法观念的说法。例如,雄辩的护教士阿诺比乌斯(Arnobius,约公元300年)指出,基督教并不可怕,自从引入基督教,“当初确立的法”并未发生改变,(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元素并未改变其属性,宇宙机器的构造(大概是天文学体系)并未瓦解,天穹的旋转、星体的升落也没有改变,太阳没有冷却,月亮的盈亏、季节的轮转、白昼长短的更替既未停止也没有受到干扰。
然而,此时(人的)自然法(natural law)与(非人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之间尚未出现截然界限。在基督纪元以来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有两条特别有意思的陈述可以表明,自然法与自然法则这两种观念多多少少还没有分开。在罗马皇帝狄奥多修(Theodosius)、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霍诺留(Honorius)于公元395年颁布的《宪法》中,有一条禁止任何人占卜,违者处以严重叛逆罪:“神秘的自然法不得为人的眼睛所见,凡违反这条原则者,就是亵渎神明。”(Sufficit ad criminis molem naturae ipsius legesvelle rescindere,inlicita perscrutari,occulta recludere,inter-dicta temptare.)这正与中国禁止占卜的谶纬之书极为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暗示了与人事进程有关而与道德无关的自然法则的存在。中国大思想家董仲舒是一个类似的有趣例子。他在公元前135年因“私自分析了两次灾异的意义”而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获得特赦。
p287
第二条叙述是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卒于228年)所提出的一段名言。他的著作在公元534年查士丁尼的《民法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中占据着相当大的部分。他在《法学说汇编》(Digest)的第一段中说:
自然法是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法。这种法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无论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由自然法产生了男女的结合,我们称之为结婚,从而有了子女的生养。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且动物乃至野兽都熟悉此法。
法学史家极力想说明这种观念对后来的法学思想从未产生任何影响。事实的确可能如此,但中世纪作家和评注家却接受了它,而且还明确表示,动物是服从神所制定法令的准“法律”个体。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那种认为自然法则就是物质(包括生物)所服从的神所立之法的观念了。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自然法不可避免地成了基督教的道德。圣保罗曾清楚地表述过这一点。圣克里索斯托姆(St. Chrysos-tom,公元5世纪初)曾在希伯来的十诫中看到了自然法的法典化。而在1148年,随着弗朗西斯科·格拉提亚努斯(Franciscus Gratianus)《教令》(Decretum)的出版,自然法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的道德,为正统的圣典学者遵奉不渝。此外,正如波洛克(Pollock)所说,中世纪的人普遍相信,君主的命令若违反了自然法,便不能约束其臣民,因此可以合法地加以抵制。这种学说总结成一句话就是,(p288)“实在法低于君主,犹如自然法高于君主”。(Positiva lex estinfra principantem sicut lex naturalis est supra)它在新教兴起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有权反抗非基督教的君主”在现代欧洲民主制的开端处也起了很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学说与孟子的儒家学说非常吻合。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不守礼,臣民有权推翻他。欧洲的社会思想家只要读过1600年以后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拉丁文翻译,肯定会注意到这种相似之处。
p288
但是,科学家及其自然法则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现在来到了17世纪。随着波义耳和牛顿的工作,自然法则的概念得到了充分发展,化学物质和行星等都“服从”自然法则。然而,很少有人研究过它究竟在哪一点上与经院哲学家的综合发生了分化。词典编纂家说,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一词第一次得到使用是在英国皇家学会1665年出版的《哲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一卷。30年后,德莱顿在翻译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中的诗句“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能认识事物原因的人最快乐)时,无意中将“自然法”一词插入,它遂成为常用语。罗布森(Robson)在其杰作《文明与法律的成长》(Civilization andthe Growth of Law)中,将“自然法”一词视为17世纪特有的观念,存在于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家的“新哲学或实验哲学”中。是齐尔塞尔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这个观念的各个形成阶段。我们也看到,亨廷顿·凯恩斯(Huntington Cairns)等法学家认为,基于人类理性的世俗化自然法和对经验自然法则的数学表达在17世纪是平行发展的。
毫无疑问,转折点出现在哥白尼(1473—1543年)与开普勒(1571-1630年)之间。(p289)哥白尼谈到了对称、和谐、运动,但从未谈到法则。吉尔伯特在其《论磁》(De Magnete,1600年)中也没有谈到法则,尽管按照他所表述的一些磁学概括,使用“法则”一词来称呼是再恰当不过了。培根的立场很复杂,在《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中,他把“自然的总法则”(Sum-mary Law of Nature)称为最高的可能知识,但他怀疑人类能否达到它;而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中,他所使用的“法则”一词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同义,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比经院哲学家进步。伽利略则和哥白尼一样,无论是在1598年论力学的《早期著作》(Jugendarbeit)中,还是在1638年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Discourses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on Two New Sciences,1638年)中,都没有使用过“自然法则”这一表述,而后一著作乃是现代力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开端。后来被称为“法则”的东西,当时是以“比例”、“比率”、“原理”等名词出现的。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斯台文(Stevin,其作品年代为1585年和1608年)和帕斯卡(Pascal,1663年),他们都未使用过法则的隐喻。
p289
令人不解的是,开普勒虽然发现了行星轨道的三条经验法则(这是用数学方式表达自然法则的最早事例之一),但他本人从不把它们称为“法则”,尽管他在其他场合使用过这个词。他的第一、第二“法则”见于《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1609年),那是用冗长的文句解述的。第三“法则”见于《世界的和谐》(HarmonicesMundi,1619年),被称为“定理”(theorem)。然而他在讨论杠杆原理时却谈到了“法则”,而且一般仿佛把这个词当作与“度量”(measure)或“比例”同义来使用。
p290
既然自然法则在天文学上起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中间去寻找这个词的最早出处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然而,在地质学、冶金学和化学等完全是另一类的科学中,却很早就有人提到它。在1546年的《论地下物的起源和成因》(DeOrtu et Causis Subterraneorum)一书中,阿格里科拉(GeorgiusAgricola)在论及关于金属成分中所含水元素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时写道:
在制备金属的每一种液体中,土究竟占多大比例,从未有人查明,更不用说解释了。这只有那一位神才知道,他给自然规定了确实而固定的法则,以把物质混合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出现在冶金化学中,至少和出现在天文学中同样早。另一则早期表述出现在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年)的著作中,他说上帝可以“到不可违犯和不可亵渎的自然法则中”(in inviolabili intemerabilique naturae le-ge)去寻找(《论无限》[De Immenso])。但布鲁诺的思想是非常“中国式的”,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欧洲人更能认识到自然现象的有机性。
与此同时,西班牙神学家苏亚雷斯(Suarez)对于澄清这个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论法》(Tractatus de Legibus,1612年)中截然区分了道德世界和非人的自然世界,并认为法的观念只适用于道德世界。他反对托马斯主义的综合,因为它忽视了这一区别。(p291)他说:“严格说来,缺乏理性的事物既不能有法,也不能有服从。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隐喻把神力的效能与自然的必然性……称为法则。”这种清晰的思考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人在把礼和法的概念推广到非人的世界时所遇到的困难。正因如此,耶稣会传教时代之后,中国人对介绍到中国来的自然法则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反应。1737年达让(d’Argens)写过一段有趣的话:
p291
一个传教士说,要让中国的无神论者相信上帝的恩典,简直要比让他相信上帝创造世界还难。我们教导他们说,上帝从无中创造了宇宙,用他那无穷的智慧立下一般的法来统治世界,万事万物皆遵守此法而呈现出奇妙的规律性。每到这时,他们就会说,这些都是空洞的言辞,他们对此毫无概念,而且对他们的理解力一点帮助也没有。他们又回答,至于我们所谓的法,乃是一位立法者所制定的一种秩序,能够迫使执法、知法、领悟法之造物去遵守。假如你说上帝曾制定过法,让能知法的存在物来执行,那么动植物及一切遵守这些宇宙法的物体就得了解宇宙法,因此就得有理解力,这是荒谬的。
在笛卡尔那里,自然法则的观念已经像在后来的波义耳和牛顿那里一样成熟。《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谈到了“上帝赋予自然的法则”。《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年)的结论中说,该书讨论了“依照力学法则物体相互碰撞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是被确凿的日常实验所证实的”。斯宾诺莎也是如此,其《神学政治论》(Trac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670年)(p292)区分了“依赖于自然必然性”的法和因人的命令而产生的法。此外,斯宾诺莎还同意苏亚雷斯的看法,认为将“法”这个词用于自然物乃是基于一种隐喻——不过是出于不同的理由,因为斯宾诺莎是泛神论者,不可能相信天界立法者这样一种幼稚的图像。
p292
齐尔塞尔认为,16世纪的经验技术是17世纪自然法则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他指出,16世纪的高级工匠、艺术家和军事工程师(达·芬奇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不仅经常做实验,而且习惯于把他们的结果以经验规则和定量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举塔尔塔利亚(Tartaglia)的《问题与发明种种》(Quesiti et In-ventioni,1546年)这本小书为例,书中给出了十分精确的定量规则来描述枪炮仰角与弹道的关系。他说:“早期资本主义工匠的这些定量规则,虽然从未称为‘法则’,却是现代物理法则的先驱。”在伽利略那里,这些规则上升为科学。
这里最基本的问题是:自然法则的观念既然在欧洲文明中作为神学的惯用语已经存在了那么多个世纪,为什么到16、17世纪会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当然,这只是现代科学在当时兴起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齐尔塞尔问道,为何在现代,上帝统治世界的观念会从自然中的例外事件(比如那些扰乱了中世纪安宁的彗星和灾异)转移到不变的规则上来呢?他的回答原则上是对的:既然统治世界的观念源于把人关于尘世统治者及其统治的构想实体化(hypostatization)到神圣领域,所以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相伴随的社会发展,以便理解现在发生的变化。事实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封建领主的权力遭到瓦解,中央集权的王权大大增加。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都有这一过程发生。(p293)而在笛卡尔从事著述的时候,英国的共和政体更把这一过程朝着一种不再属于王权的中央集权推进。如果我们可以把斯多亚派的宇宙法学说与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各个君主政体的兴起联系起来,那么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把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法则概念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时王权专制的出现联系起来。齐尔塞尔说:“让·博丹(Jean Bodin)的主权论出现之后仅仅40年,就发展出了把上帝看成宇宙立法者的笛卡尔观念,这绝不仅仅是巧合。”就这样,这个在“东方专制主义”环境中诞生的观念以基本形式保存了两千年,终于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环境中获得了新生。
p293
克隆比(Crombie)的新近著作揭示出的一桩事实颇能说明齐尔塞尔的解释。他说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年)曾明确使用过“自然法则”这一表述,但该表述在13世纪并未流行起来。例如,罗吉尔·培根写道:“我已在讨论几何学的论著中表明,反射、折射法则是一切自然活动所共有的。”他又说,幻觉必定“不会超出自然在世界诸物体中保存的法则”。但他相信灵魂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些法则,因为他说在扭曲的神经中,灵魂的力量“使(所见之物的)种相(species)不再遵守通常的自然法则,而是按照符合其运作的方式起作用”。倘若罗吉尔·培根实际在说,生命有机体内的过程所服从的法则比无机世界的法则更高,那么可以说他的这种观念非常先进。但无论如何,物质和光的法则的观念在当时根本不为一般人所接受。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新的政治专制主义和实验科学的诞生才把这种观念唤醒,使之成为引人注目的谈论话题。
p294
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只要说,在盖伦、乌尔比安和狄奥多修《宪法》的时代与开普勒、波义耳的时代之间,一切人所共有的自然法观念与一切非人事物所共有的自然法则观念已经完全分开了。这一点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关于自然法与自然法则的思想发展和欧洲有什么不同。
古代道家思想家(公元前3、4世纪)虽然深刻而富有灵感,但或许因为他们非常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所以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于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他们因为欣赏相对主义以及宇宙的博大精微,所以在未奠定牛顿式世界图景的基础之前就在摸索一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景。科学沿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这并不是说宇宙万物的秩序“道”不遵守尺度和规则,而是道家往往把道看成理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也许可以说,由于数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把科学交给道家掌管,所以中国科学只能在一种大体上经验的层面上发展。此外,对于实在法来说,道家的社会理想比其他学派的理想更无用;他们试图回到原始部落的集体主义中去,那里一切都没有明文规定,一切事情都在社群合作中顺利进行,因此他们对任何立法者的抽象法都不会感兴趣。
另一方面,墨家和名家一起极力改进逻辑程序,并率先将其用于动物学的分类以及力学和光学的基本原理。我们不知道这场科学运动为何失败了,也许这是因为墨家对自然的兴趣和他们在军事技术上的实用目的结合得太紧密了。无论如何,这两个学派在中华帝国第一次统一剧变(公元前230年)之后便不复存在了。名、墨两家似乎并不比道家更接近自然法则的观念。如何恰当地翻译《墨经》逻辑中的专门术语“法”仍然很有争议,但就目前所见,墨家是在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原因”非常相似的意义上使用“法”的。
p295
法家与儒家只对纯社会问题感兴趣,对于人周围的外在自然没有任何的好奇心。法家全力强调实在法的重要性,那纯粹是立法者的意志,可以不顾普遍接受的道德,而且如果国家需要,还可以违反这些道德。但无论如何,法家的法都是精确而抽象地制定的。而儒家则固守古代的风俗习惯和礼仪,包括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本能地认为是正当的所有那些行为,比如孝道——这就是“礼”,我们可以把它等同于自然法。此外,这种正当的行为须由家长式的地方官来教导,而不能强制。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则恰当地借用了水利工程上的一个东西来作象征,把良好的习俗比喻成堤防,谓已然者易知,未然者不易察。良好的习俗因比成文法更加灵活而能防患于未然,而法律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能起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战胜法家之后支配中国人思想的一种观点了:既然合于礼的正确行为总是依赖于环境,比如依赖于社会关系中当事各方的身份,那么在事先颁布不足以应对具体复杂环境的法律就是荒谬的了。因此,成文法被严格限于纯刑事的规定上。
我们已经讨论了礼与法的区别,这两个字都不容易用于非人的自然。但有一个中国古字似乎可以把非人的现象与人法联系起来,那就是“律”。在中国的法典中,律代表“法令”和“规章”。这种含义无疑很早就有了,比如《管子》说:“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这里,“律”的观念非常接近于康福德(Cornford)所讨论的 μopa[命运、必然性]以及其他希腊观念。但“律”还有一种相当不同的含义,即古代音乐和声学中使用的一组标准竹制律管以及这些竹管所代表的12个半音。那么声律与人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呢?
p296
“律”字右边的声符(聿)象征一只手持着书写工具,其左边的部首(彳)意指左脚迈步(亍则是右脚迈步),这暗示“律”原与仪式舞蹈的记号有关。后来,由于十二个半音用来对应一年的十二个月,“律”字便有了历书日期之意,于是在历法的篇名中与“历”字合用,例如《前汉书》中的“律历志”。问题在于,法、法令、规章的观念是如何可能从表述标准乐音的“律”字衍生出来,甚或与之相联系的。
也许刚才提到的词源学上的考虑提供了一条线索。从占卜者或巫师为音乐和仪式舞蹈所做的指导,到尘世统治者为其他行为,尤其是有组织的军事行为所做的指导,其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跳舞以驱鬼和操练兵器以对付敌人在逻辑上是类似的。葛兰言说,有几种舞蹈确实要佩戴和挥舞兵器。有人认为,舞场周围原分五区,后来就用每一区放置的乐器名来给某种音质命名,后来又给不同的音调命名。
仪式舞蹈、军事活动的指令与音律之间显然有一种一般关联。但这里并非暗示中国人曾经认为,标准律管的半音音程源于或构成了自然现象世界当中的任何一种法则。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一个物理学分支,竟然源于一个具有人类法规含义的字,这一事实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包含着自然法则观念的要素。
如果现在有读者翻阅一下写于公元前90年左右的《史记·天官书》,他可能会看到以下文字:
p297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
根据本次演讲中的整个讨论,该读者一定会确定,不论司马迁实际上说了什么,他都不是在科学的自然法则意义上谈的“度”(“此其大度也”),因此“度”字需要我们注意。
“度”的原义是“量度”,不仅词典编纂者认为这是其最常见的用法,而且许多最重要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索引也这样标示。其词源,比如从甲骨文形式推断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它是如何具有这种含义的。不过,“度”也可能有“法”的含义,尤其是它与别的字连用组成“制度”、“法度”等词时。顾赛芬(Couvreur)曾经给出过《易经》中出现“制度”的例子,以及《尚书》中“度”字单独出现、表示某些人“超越了界限”或“僭越”的例子。当然,由于每种法都有某个定量方面,所以“法”与“度”之间当然有一种密切的语义关联。我们说,“在多大程度上某某行为才会受到某某法律条文的约束”?或者“必须通过细则措施来抑制某某活动的滋长。”但是在立法者制定独立于道德的实在法(例如秦始皇开始规定车轮尺寸)之前,这种定量方面往往只是隐喻性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战国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他们常常把人类社会的法比作木匠的规、矩和铅垂线。
更重要的是,正如顾赛芬所指出的,可以认为“度”是描述天体运动的一个明确的专业术语。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个字一直被用于把天球分成的365%度,也被用于其他许多划分刻度,比如漏壶(水钟)上显示的把一昼或一夜分成100度。(p298)董仲舒在大约与司马迁同时的《春秋繁露》中说的一句话很有启发性,他说“天道有度”,即天道有其规则整齐的运动。我们现在必须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就严格的科学哲学标准而言,将单独出现的“度”字译成“普遍法则”是不恰当的,更好的说法应该是:“这些现象都有其规则的、整齐的(或可量度的)循环运动。”
p298
我们希望能问司马迁这样一个问题:你在使用“度”这个字时,是否意指它具有“法”的潜在含义呢?如果是,那么是谁的法呢?我相信他极不可能回答说:“是上帝之法”(天界的统治者)。他几乎肯定会说,那是“自然度”(自然的整齐运动)或“天道度”。
在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宇宙论思想方面,我们可以从一部早期的偏僻著作中找到适合我们目的的讨论。这部著作就是《计倪子》,其中只有一部分内容留传至今,现收录于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供书》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计倪子[又名计然]是真有其人,还是伪托范蠡之名写此书的作者所杜撰的人物。范蠡本人是公元前5世纪南方越国的政治家。但从书内证据判断,计倪子与越王勾践的讨论当不会写在邹衍时代(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当然,书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可能是汉人的杜撰,但我们得承认,书中包含了一些相当古老的材料,比如鬼神的名称,传说中五行的主宰等。考虑到这种来源,也许可以把该书的年代定为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初,并视之为南方自然主义传统的体现。由于书中载有一些有趣的植物和矿物,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留传至今的中国最早科学文献之一。无论如何,其确切的成书年代与出处并不影响我们目前的论点。
p299
在《内经篇》也存在于《越绝书》中),我们看到有下面一段话:
越王曰:“善,论事若是其审也,物有妖祥乎?”计倪对曰:“有,阴阳万物,各有纪纲。日月星辰刑德,变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胜,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顺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从其德而避其衡。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顷也,欲变天地之常数,发无道,故贫而命不长。是圣人并苞而阴行之,以感愚夫,众人容容,尽欲富贵,莫知其乡。”越王曰:“善。”
在这段引人注目的深奥的话中,异常现象被剥去了一切超自然性质,表明是更正常现象的一部分。就当时而言,这种思想的确非常先进,因为极端的统计涨落被视为与正常现象完全自然的偏离。无论涨落有多大,也绝非“上帝所为”。旱灾和水灾,疾病或蝗灾,虽然出现的时间好像很不规则,而且给人和社会带来了很大问题,但经过长期反复,就可以从原则上对其进行预测,贤明的统治者就可以尽早保护自己和他的百姓。①不够谨慎的人很容易把“纪纲”译成“自然法则”。福克(Forke)小心翼翼地把它译成”bestimmte Wandlungen”[固定的变化]。但词典编纂者承认,这个词带有人法的含义。
——
①与这种思维相似的西方思维与扰动论(theory of perturbations)有关。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动物的发育异常是“自然的,但并非出于本性”。经过亚里士多德评注家辛普里丘(Simplicius)和菲洛波诺斯(Philoponus)的努力,外在因素导致局部异常并使之包含在正常整体之中的观念进入了经典力学。
p300
若从词源上看,我们这里显然必须讨论一下与织物的类比,“纪”和“织”皆以“纟”为部首。“纪”将“纟”与“己”结合起来,它来源于一个不明确的甲骨文,意为“把丝线一根根理顺、有序排列、管理、统治、法律、规范、规则系列、纪年周期、日月相合、铭刻的纪年”。我们知道,最显著的纪年周期是木星周期。《计倪子》也引人注目地谈到了木星周期,且把它定为12年。“纲”字将“纟”与“冈”结合起来,古体字的声旁显示一张网和一个人。其原义是织成网边的绳子,后来指“统治、管理、处置、排成秩序、指导”,尤其是与“纪”连用时。与之相似的“网”字虽然含义更加局限于“罗网”之义,但后来开始具有处罚和法律的意味,这可能是因为《道德经》曾用“网”字做过这样的比喻(“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值得注意的是,对“纪”、“纲”二字的若干种解释都蕴含着一个主动的动词,如理顺、有序排列、统治、制定法律等,这些解释都源于《诗经》(成书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中对“纪纲”一词的最早使用。《诗经》中说,“纲纪四方”,即君王规定其法纪和习俗。然而,我们不应过于严格地从实在法的角度来思考它,因为公元121年出版的《说文》中经常提到“三纲六纪”,公元80年出版的《白虎通德论》则有一整卷把纪纲解释为人类社会中颠扑不破的关系线索,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等。这样我们就再一次遇到了中国的自然法,而“纲纪”的确作为这种含义的一个法律术语频繁出现在汉代书籍中。如果古代君王颁布纪纲,那么他们只是承认有某种人类社会之道比他们自己伟大得多而已,而并非随意将己意加诸四方。如果回到非人的自然世界,情况也是一样。《计倪子》一书明确否认有一个超自然的“使人解脱者”(disentangler)或超人格的立法者存在。(p301)书中说,自然的巨大涨落不论因为人的疏于准备而酿成多大灾难,它也只是万物之道中正常阴阳进程的一部分。万物皆在运动,但并不一定要有一个驱动者。事实上,这种道是自发的,不是被创造的,并没有一个对道进行控制的天界主宰能被祈祷和恳求所打动。君王须注意提防,储藏谷物以备不测,不浪费老百姓的生计,还要尽可能深地研究自然的运作以预知未来,这样社会中的人就可以摆脱环境的约束而获得自由。
p301
对适用于非人自然的“纲纪”或“纪纲”的定义和解释还可见于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计倪子》与这些医学文献有一种奇特的密切关联(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医学文献及其详细注解确证和扩展了词源学考虑使我们做出的解释。在《计倪子》中,作者先是描述了传说中的黄帝给五方(东西南北中)的土地神指定的工作,然后说:“并有五方,以为纲纪。”这正是宇宙的动态样式(dy-namic pattern)。事实上,一张网显然很接近于一种巨大的样式。整个宇宙中有一张关系之网,其节点是事物和事件。它不是任何人编织成的,但如果你干扰了网的结构,就会冒风险。接下来我们将追溯这张无编织者的网、这种宇宙样式的后续发展,直至探讨到中国人接近发展出某种成熟的有机论哲学为止。
这些观念在医学经典著作中被视为理所当然。故《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道:“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唐代和明代的注家又各自给出了进一步的理解。例如马莳说:“万物得是阴阳而统之为纲,散之为纪。”张介宾说:“阴阳为天地之道,总之曰纲,周之曰纪。”因此,它们讨论的同样不是任何立法者的法,而是所有特定事物相对于自然的关系之网中其他事物的固定组成和运动。
p302
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任何清晰的证据来表明中国人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法则观念。由于我们仍要讨论那些自称儒家的学派,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向宋代的理学家(公元12世纪)。朱熹及其群体的其他思想家曾力图把整个自然和人纳入同一个哲学体系,他们所研究的主要概念是“理”和“气”“气”大约对应于物质,或者毋宁说对应于物质和能量,而“理”则近似于道家所说的作为自然秩序的“道”,尽管理学家也在一种略为不同的专业意义上使用“道”字。“理”可以解释为宇宙中的秩序原则和组织原则。布鲁斯(Bruce)、韩克(Henke)、瓦伦(Warren)以及比较晚近的卜德(Bodde)都把“理”译成“law”(法),但根据我的判断,这样译是不恰当的,而且可能导致巨大的混淆,因此应当放弃这种译法。
“理”最古老的含义是事物的纹理、玉的斑纹或肌肉的纤维,用作动词时指按照事物的自然纹理切割它们。由此它获得了通常的字典含义,即“原则”。但它无疑一直保留着“纹理”的含义,朱熹本人也确证了这一点,他说:
“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如这竹篮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条子恁地去;又别指一条曰,一条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许多理。”
p303
因此,理其实是自然的秩序和样式,而不是成文法。但理并不是某种像马赛克那样死板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一切生命体、人类关系和最高人类价值中的动态样式。这种动态样式只能用“有机论”(or-ganism)一词来表达,而理学其实是一种力图成为有机论哲学的思想体系。
于是在12世纪下半叶,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非常类似于近一千年前欧洲的乌尔比安所表达的观点,这种观点曾被吸收到了查士丁尼的《法学说汇编》之中。但一个深刻的差异在于,乌尔比安毫不含糊地谈到了“法”,而朱熹则主要依赖于一个首要含义为“样式”的术语。对于乌尔比安(和斯多亚派)而言,万物皆是服从一种普遍法的“公民”;而对朱熹而言,万物皆是一种普遍样式的要素。总的来说,关于自然法则的概念,除某些迹象以外,在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学派——宋代的理学家那里似乎找不到更多东西了。他们强调某种不同的东西,虽然这最终对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
另一个中国字“则”常被试图译为“自然法则”。在大天文学家张衡(78-139年)的官方传记里有一句话:“天步有常则。”(即行星和星座在给定时间内所行经的度数,星辰的升落等等都遵循不变的规则。)但也有人怀疑人类是否有可能理解在自然万物中运作的“则”。我想举的第一个例子出自《楚辞集注》中贾谊的诗作《鵩鸟赋》(约公元前170年):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p304
第二个例子出自王弼的《周易注》(约公元240年),他在解释第十卦——“观”卦时说:
统说观之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观感化物者也。神则无形者也。不见天之使四时,而四时不忒;不见圣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这也许是最有启发性的一段话了。我们看到他断然否认有一位天界立法者在对四季(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行)发号施令。这种思想是极端中国式的。普遍和谐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天上发布的命令,而是源于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合作。实际上,“则”是体现在每一个个体事物内部的存在规则,个体藉此规则而在整体中有其地位和功能。我们可以看到,理学家的有机论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思想。用怀特海的习语来说就是,“原子并非盲目地奔跑”,如机械唯物论所假定的;万物在运行过程中也不会具体受到神的干预,如唯灵论哲学所假定的;而是说,所有层次的东西都会按照它们在更大样式(有机体)中的地位来行动。因此,“则”绝不意指任何类似于牛顿意义上的自然法则的东西,这种解释也不能恰当地说明理学家关于“理”的思想。
中国人之所以断定天没有命令自然过程去遵循其常规,是因为“无为”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天界立法者的立法便是“为”,是在强迫万物服从,是在强加制裁。不错,自然显示出一种永恒的规律性,但这并不是一种命令式的永恒和规律性。正如荀子(约公元前240年)所说,天道是一种常道,自然的秩序是一种不变的秩序,但这并不等于肯定有人在下命令。
p305
《礼记》中有一段杜撰的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鲁哀公问,关于天道,什么最可贵?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
这里同样是对任何上天创造或立法的否定,即使是一种含蓄的否定。顺便指出,虽然道家特别强调“无为”的概念,但它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一切古代思想体系的共同基础的一部分。
这里不妨再谈一谈这种深刻的观念。要想在古书中找上天无为而行事的观念一点也不难。它充斥于《道德经》的字里行间,比如“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这种观念其实是道家的常识,在《文子》之类的书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中也出现过。《吕氏春秋》(约公元前240年)对天道运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
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
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
这种观念的确崇高,但与天界立法者的观念极不相容。天体的运行遵循的是不教之教、无言之诏,(p306)而开普勒、笛卡尔、波义耳和牛顿所相信的、启示(“启示”一词显示了西方思想的自发背景)于人心的自然法则却是一个超人格、超理性的存在所颁布的法令。虽然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是一种隐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没有很大的启发价值。
p306
因此,我的结论是,理学派是在一种怀特海式的有机论意义上来理解“法”的。我们不能说朱熹和理学家们在定义“理”时心中完全没有牛顿意义上的“法”的观念,但它起的作用很小,其主要成分是“样式”,是最活跃、最生动的样式,因此是“有机论”。这种有机论哲学包含了宇宙万物:天、地、人具有同一个理。
在欧洲,可以说自然法因其普遍性而帮助过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由于自然法从未被认为是法,而是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礼”,所以很难设想它能适用于人类社会之外,尽管相对而言,它比欧洲的自然法要重要得多。在整个自然中运作的秩序、系统和样式不是作为“礼”,而是作为道家的“道”或理学家的“理”。“道”与“理”都是神秘难解的,都没有法学内容。
在欧洲,同样可以说实在法因其精确的表述而帮助过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因为它鼓励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一个与尘世立法者相对应的天界立法者,其命令遍及一切物质事物。为了相信自然是理性可以理解的,西方人不得不假定(或者方便地预先假定)有一个本身是理性的至高存在安排了这种可理解性。
这使我们回到了道家。道家虽然对自然深感兴趣,但并不信任理性与逻辑。墨家和名家完全相信理性与逻辑,但如果说他们对自然感兴趣,那只是出于实际的目的。法家和儒家则对自然丝毫不感兴趣。(p307)而在欧洲历史上,经验的自然观察者与理性主义思想家之间的鸿沟从未达到这种地步。正如怀特海所说,这也许是因为欧洲思想过分受制于一个至高造物主的观念,该造物主自身的合理性保证了其造物是理性可以理解的。无论人类现在的需求是什么,这样一个至高的上帝不可避免会是人格的。但这在中国思想中是看不到的。即使是今天,中国人也把 Laws of Nature译成“自然法则”,这种译法坚定地保持着古代道家对人格神的否定,以致成了一个近乎自相矛盾的术语。
p307
这里我们无法研究古代中国人的上帝观。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一直在就欧洲术语的正确翻译大加争论,自那以后,讨论这一主题的文献可以说浩如烟海。由于当时的汉学研究才刚起步,大部分文献现在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我们知道,古代中国人用“天”或“上帝”来称呼God,不过有时也用其他词,比如《庄子》中的“宰”。“天”的古字无疑是一个拟人化的图形(可能是一个神),而“帝”的古字也是如此,尽管还不能完全确定。我认为与“鬼”有关的“宰”也是如此。许多汉学工作都是基于古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有这些观念的人格化,其得出的结论很难加以概括。在这方面有很多种说法:例如顾立雅认为“上帝”是皇帝功能的超越化,葛兰言认为“上帝”是四季时序的人格化,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则认为“上帝”和天都是原始祖先的象征。顾立雅提出了现在一般公认的观点,认为“上帝”出现在商代,而“天”则是较晚的周代用语。戴观一(Tai Kuan-I)认为“上帝”之名是中国人从苗族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无论如何,有三点是清楚的:(1)古代中国所认识和崇拜的最高神灵并非希伯来人和希腊人意义上的造物主;(2)无论最高的神是人这一观念在古代中国思想中走了多远,(p308)它都不认为有一个神圣的天界立法者给非人的自然颁布了法令;(3)最高的神这一概念很早就是非人格的。这并不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之中没有秩序,而是说,这种秩序并不是由一个理性的人格存在所规定的,因此不能保证其他理性的人格存在能用他们自己的尘世语言详细说明预先存在的神圣法条。中国人不相信自然法则的法条可以被揭示和解读,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有一个比我们更加理性的神性存在曾经制定过这样一套可读的法令。事实上,我们觉得道家会把这样一种观念斥为过于幼稚,不足以说明他们所直觉到的微妙而复杂的宇宙。
p308
总之我认为,自然法则的观念之所以没有从中国人一般法的观念发展出来,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过渡期间,中国人对法家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很不喜欢精确表述的抽象的成文法;第二,当官僚体制最终建立起来时,事实证明,“礼”的旧有观念要比任何其他观念都更适合典型的中国社会,因此,自然法的要素在中国社会要比在欧洲社会更为重要。但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写成正式的法律条文,且其内容又以人和伦理为主,因此无法将其影响领域拓展到非人的自然;第三,像“一个至高存在”这样的观念虽然肯定从很早就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人格性,这些观念严重缺乏创世的想法,因此中国人不相信有一个天界立法者在创世之初就给非人的自然规定了一套精确表述的抽象法则,也不相信其他较低的理性存在者能用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来破解或重新表述这些法则。
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他们认为,万物之所以能够和谐并作,(p309)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于它们的最高权威在发布命令,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各个部分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样式,它们服从的乃是自身本性的内在命令。现代科学和有机论哲学及其整合层次已经回到了这种智慧,并且被我们对宇宙演化、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的新认识所加强。但谁能说那个牛顿阶段不重要呢?最后,处于这种宇宙观背后的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力量,这些力量促使中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官僚制度,在每一步都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和哲学。倘若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从根本上有利于科学,那么本次讲演中讨论的抑制因素也许就都能克服了。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一定是非常有机和非机械式的。
p309
在结束本文之前,让我们举一个显著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与欧洲在自然与法方面的看法差异。人们都知道,欧洲中世纪的法庭曾多次对动物做出审判和刑事起诉,接着往往是以适当方式处以死刑。学者们曾不辞劳苦地搜集了有关这些案件的大量材料。这些案件的发生频率成一条曲线,在16世纪达到显著的高峰,从9世纪的三例升至16世纪的六十例左右,再降到19世纪的九例。我们怀疑这是否如埃文斯(Evans)所说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早期记录。16世纪的高峰对应着女巫狂热(witch-mania)。对这些案件的法律诉讼分为三类:(1)对家畜伤人的审判和处决(如处决吞吃婴儿的猪);(2)对传染疾疫的飞禽或昆虫加以驱除或诅咒;(3)对“自然的反常”(lusus naturae)(如公鸡生蛋)加以定罪。对我们目前的主题来说,后两种类型最值得注意。1474年,巴塞尔曾有一只公鸡因产卵而犯了“令人发指的违反自然之罪”而被判活活烧死。(p310)迟至1730年,瑞士也有一起同样类型的起诉事件发生。造成惊恐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认为“公鸡之卵”(euf.)是巫师药膏的一种成分,从这种卵中会孵出极毒的蛇。但有趣的是,这类审判在中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中国人不会如此自命不凡地认为已经充分认识了上帝规定让非人之物遵守的法则,而对违法的动物进行控告。恰恰相反,中国人的反应必然是把这些罕见而吓人的现象当成“谴告”(上天的谴责),地位被危及的将是皇帝或地方官,而不会是那只公鸡。让我们具体加以引证。《前汉书·五行志》中有几处提到了家禽和人的性反转。这些事件被归于“青祥”一类,被认为与五行中木的活动有关。它们预示当政者会遭到严重伤害。
p310
至于上述三种类型中的第二种,有趣的是,中世纪欧洲人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他们有时认为田鼠或蝗虫破坏了上帝的法律,因此要受到人的控诉和定罪,但有时又认为田鼠和蝗虫是被派来警告人类悔过自新的。
极其有趣的是,自拉普拉斯的时代以来,欧洲人就觉得可以不需要上帝这一假说作为自然法则的基础,就此而言,现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回到了道家的观点。这正说明了为什么许多道家著述读起来会有那种奇特的现代感。但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不经过一个“神学”阶段能否达到它目前的状态,这仍然是个问题。
当然,在现代科学看来,自然“法则”中已经没有了命令与义务的观念残余。正如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说,自然法则现在被视为统计上的规律性,只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或大小范围内有效,是描述而不是规定。从马赫(Mach)到爱丁顿(Eddington),(p311)人们一直在激烈争论科学法则的表述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主观性,这里我们无法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了。问题在干,如果不走西方科学实际所走的道路,我们能否认识到统计规律性及其数学表达呢?假如某种文化想产生开普勒式的人物,是否一定要有那种将产卵的公鸡依法起诉的心态呢?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Sam Wolf摄于 1968年,感谢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照片)
目录
导言 1
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4
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44
科学与社会变迁 111
4.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 142
5.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165
6.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176
7.时间与东方人 203
8.人法与自然法则 280
附:台译本序 312
===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