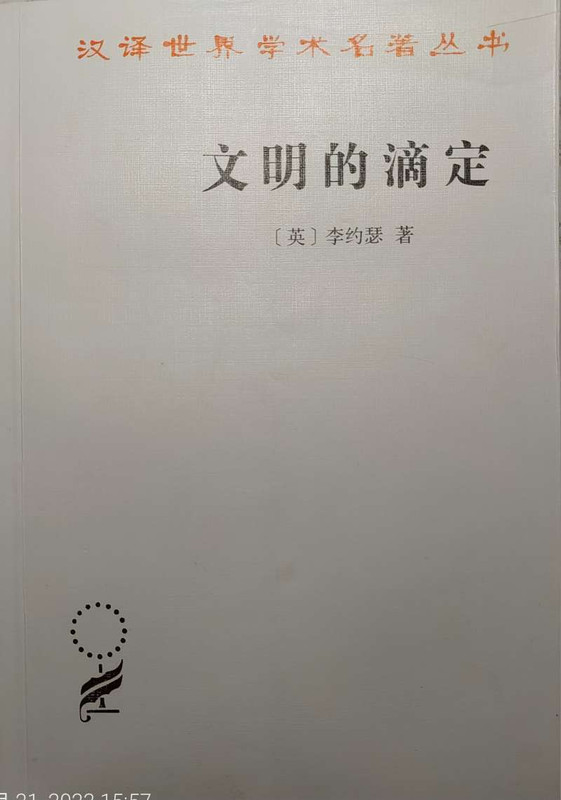zhbglzx
【书摘】李约瑟《文明的滴定》1.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 哲学和神学的因素
《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英〕李约瑟 著
张卜天 译
… ·正文约4400字;
·粗体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
摘要
“滴定”是指用已知强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前者将后者完全转变为第三种化合物,转变的终点由颜色变化等方式来确定。这就是所谓的“容量分析”或“滴定分析”。(p2)
才华横溢的发明天才达·芬奇仍然生活在这个原始的世界中;而伽利略则突破了它的藩篱。因此有人说,中国的科学技术直到很晚仍然是达·芬奇式的,伽利略式的突破只发生在西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出发点。
直到因为与数学结合而被普遍化,自然科学才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技术要素可以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而科学要素通常却未能如此。(p5)
在儒家思想中,伦理行为带有圣洁性,但与神和神性并无关系,因为造物主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不必要的。
不幸的是,道家虽然对自然极感兴趣,却常常不相信理性和逻辑,因此道的运作往往有些不可思议。
儒家把兴趣纯粹集中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上,道家虽然对自然的兴趣很强烈,但这种兴趣往往是神秘的、实验的,而不是理性的、系统的。
这里的核心特征之一无疑是中西方自然法(laws of Nature)观念的差异。
在西方文明中,法学意义上的自然法观念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观念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
西方文明中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无疑是这样的:正如人间的帝王立法者能够颁布成文法典让人们遵守,天界最高的理性造物主必定也颁布了一系列法典让矿物、晶体、植物、动物和星体遵守。(p23)
中世纪构想出来的朴素形式的自然法观念对于现代科学的诞生是否是必不可少的?
在基督教时代,由于受到希伯来人的影响,立法之神的观念被极大地推进了。在整个中世纪,神为非人的自然立法这一观念多多少少是一种常识,但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隐喻才开始得到重视。
中国人很早就不喜欢精确表述的抽象成文法,那是从封建制度过渡到官僚制度过程中法家政客的失败暴政中制定出来的。
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写成正式的法律条文,且其内容又以人和伦理为主,因此无法将其影响领域拓展到非人的自然。
中国人不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来破解或重新表述一个理性的至高存在所制定的法。
如果不走西方科学实际所走的道路,我们能否认识到统计规律性及其数学表达呢?(p25)
正文
导言
p1
中国、印度和欧洲——闪米特的文明是世界三大历史文明,但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文明对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希腊人的伟大思想和制度,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中国人总体上遥遥领先于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晚期发生科学革命,欧洲才迅速领先。但是在那之前,不仅在技术进程方面,而且在社会的结构与变迁方面,西方都受到了源自中国和东亚的发现和发明的影响。除了培根爵士所列举的三项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罗盘),还有其他上百种发明,比如机械钟、铸铁法、马镫、有效挽具、卡丹环[Cardan suspension]、帕斯卡三角形、弓形拱桥、运河水闸、船尾舵、纵帆航行和定量制图法等,都对社会更不安定的欧洲产生了影响,有时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相对的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科学所蕴含的各种政治优势)只能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呢?只有认真分析东西方文化,对其作一种真正的滴定(titration),才能最终回答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思想和哲学上的许多因素都起了各自的作用,但肯定也有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需要加以研究。
每个人在学校都学过基础化学,所以谈论“滴定”没什么好怕的。大多数人都操作过滴定管,见过化学反应完成时的颜色变化。在通常的词典中,词典编纂并没有很好地定义这个词,但我们也许可以说,(p2)“滴定”是指用已知强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前者将后者完全转变为第三种化合物,转变的终点由颜色变化等方式来确定。这就是所谓的“容量分析”或“滴定分析”,它的发明时间要比我们认为的更晚。1782年,居顿·德莫沃(Guyton de Morveau)最先使用了这一方法,但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将该技巧完全系统化,并且在1819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其进行了描述。不过,当时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因为直到1864年,“titration”一词才第一次被使用——它无疑源自法文词 titre,很久以前试金者(assayist)用这个词来表示合金中的黄金纯度。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发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亚述的第一条灌溉渠出现在公元前690年,中国的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意大利的第一副眼镜出现在公元1286年,等等。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查明之后当赞许则赞许,所以我们也必须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
p2-3
因此,我把在各种场合写的一些论文、演讲和随笔合在一起,冠名为“文明的滴定”。本书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①相类似,但内容并不重复。在我的朋友安生(Ruth Nanda Anshen)的建议下,我将这些文章集合成书,希望能对比较知识社会学中这个伟大而悖谬的主题做出阶段性说明。最后,我要感谢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合作者们——王铃、鲁桂珍、曹天钦、何丙郁,三十年来,他们日日夜夜陪伴我辛勤发掘。如果没有他们,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间的文明壁垒就不可能有丝毫突破。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的聪慧使我的文字变得清晰易懂。
——
①李约瑟与王铃(王静宁)、鲁桂珍、何丙郁、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曹天钦等人合作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Cambridge,1954)共七卷十二部分。以下此书简称SCC。
—— 李约瑟
1.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①
(1)导言 p4-5
(2)传统中国的科技面貌 p5-10
(3)中国与西方的对比 p10-13
(4)科学家和工匠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地位 p13-20
(5)封建官僚社会 p20-21
(6)发明与劳动力 p22
(7)哲学和神学的因素 p23-25
(8)语言因素 p26-27
(9)商人的角色 p27-28
(10)新科学在旧世界的起源 p29-43
(1)导言
p4
在下文中,我将与欧洲进行对比,试图描述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发明传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长处和弱点。当然,此标题的灵感来自于19世纪法国作家创造的某些名言。我指的是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所写的军事生活的“奴役与伟大”(Servitudes et grandeurs),以及后来因巴尔扎克而不朽的娼妇生活的“辉煌与悲惨”(Splendeurs et misères)。如果我们沿着旧世界不同区域的人认识和控制自然的路径进行回溯,便会清楚地看出东西方的长处和弱点。我想先描述一下中国和欧洲传统在自然科学方面(无论是纯粹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的一些明显差异,再谈谈科学家和工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最后联系哲学、宗教、法律、语言以及具体的生产环境和商品交换来探讨科学的某些方面。
——
① Scientific Change(Report of History of Science Symposium, Oxford,1961), ed. A. C. Crombie, London, 1963。
p5
首先,我们必须界定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我在两者之间作了一项重要区分。当我们说现代科学只在文艺复兴晚期的伽利略时代发展于西欧时,我们的意思当然是指,只有在彼时彼地才发展出了今天自然科学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把数学假说应用于自然,充分认识和运用实验方法,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空间的几何化,接受实在的机械论模型。原始的或中世纪的假说与现代假说显然大不相同,它们因其内在的本质模糊性总是无法得到证明或否证,而且容易在空想的认知关联系统中结合在一起。人们以先验构造的“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或数秘主义(number-mysticism)的形式来摆弄这些假说中的数,而不是把它们用于后验比较的定量测量。我们都知道原始的和中世纪的西方科学理论,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盖伦的四体液说,普纽玛(pneumatic)的生理病理学说,亚历山大里亚原化学的共感(sympathies)与反感(antipathies)说,炼金术士的三本原(tria prima)说,卡巴拉犹太神秘学(Kabbala)的自然哲学等,但却不太晓得其他文明也有相应的理论,比如中国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致的卦爻系统等。在西方,才华横溢的发明天才达·芬奇仍然生活在这个原始的世界中;而伽利略则突破了它的藩篱。因此有人说,中国的科学技术直到很晚仍然是达·芬奇式的,伽利略式的突破只发生在西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出发点。
直到因为与数学结合而被普遍化,自然科学才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世纪世界的科学是与它所从出的种族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文化的民族要想找到任何共同的讨论基础,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发明不能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自由传播——事实上,这些发明大都是从东方传到西方。但与种族相关的概念体系相互之间无法理解,这的确严重限制了科学思想领域中可能的接触和传播。因此,技术要素可以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而科学要素通常却未能如此。
p6
尽管如此,不同文明之间的确有过非常重要的科学交流。我们现在很清楚,在科技史上必须把旧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甚至连非洲也要包含进来。但是当我们采用这种普世观点时,却出现了一大悖论。为什么带有高技术含义的现代科学,自然假说的数学化,只是在伽利略时代才迅速兴起呢?许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但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东亚文化要比西欧有成效得多?只有对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同时不忘观念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才能最终说明这两件事情。
(7)哲学和神学的因素
p23
显然,我们最终必须在儒家 —— 道家世界观对科技的影响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科技的影响之间进行一种详尽的比较。众所周知,支配中国文人心灵两千多年的儒家从根本上是入世的。他们持有一种社会伦理学,旨在指出一条道路,使人能在社会中和谐共处,幸福生活。儒家关心人类社会,关心西方人所谓的自然法,即人应当追求的那种符合人的实际本性的行为方式。在儒家思想中,伦理行为带有圣洁性,但与神和神性并无关系,因为造物主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不必要的。而道家则是出世的,他们的道是自然的秩序,而不只是人类生活的秩序,道以一种奥妙的有机方式运作着。不幸的是,道家虽然对自然极感兴趣,却常常不相信理性和逻辑,因此道的运作往往有些不可思议。因此,儒家把兴趣纯粹集中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上,道家虽然对自然的兴趣很强烈,但这种兴趣往往是神秘的、实验的,而不是理性的、系统的。
这里的核心特征之一无疑是中西方自然法(laws of Nature)观念的差异。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对东亚和西欧文化中的自然法概念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很容易表明,在西方文明中,法学意义上的自然法观念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观念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西方文明中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无疑是这样的:正如人间的帝王立法者能够颁布成文法典让人们遵守,天界最高的理性造物主必定也颁布了一系列法典让矿物、晶体、植物、动物和星体遵守。这种观念无疑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科学之所以只在欧洲产生,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种观念呢?换句话说,中世纪构想出来的朴素形式的自然法观念对于现代科学的诞生是否是必不可少的?
p24
毫无疑问,是巴比伦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位天界立法者为非人的自然现象“立法”的观念。太阳神马尔杜克(Marduk)被描绘成众星的立法者。将这种观念继续下去的与其说是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不如说是斯多亚派,他们构想了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宇宙法,既适用于人,也适用于非人的自然。在基督教时代,由于受到希伯来人的影响,立法之神的观念被极大地推进了。在整个中世纪,神为非人的自然立法这一观念多多少少是一种常识,但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隐喻才开始得到重视。转折点出现在哥白尼与开普勒之间。哥白尼从未使用过“法”这一表述,开普勒虽然用过,却并未将其用于他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我们奇怪地发现,“法”这个词在最初用于自然现象时并未出现在天文学或生物学领域,而是出现在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一部著作中,其上下文讨论的是地质学和矿物学。
中国人的世界观则依赖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他们认为,万物之所以能够和谐并作,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于它们的最高权威在发布命令,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各个部分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样式,它们服从的乃是自身本性的内在命令。自然法的观念之所以没有从中国人一般法的观念发展出来,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人很早就不喜欢精确表述的抽象成文法,那是从封建制度过渡到官僚制度过程中法家政客的失败暴政中制定出来的。(p25)其次,当官僚制度最终建立起来时,事实证明,表现为业已接受的习惯和好风俗的旧的自然法观念最适合 典型的中国社会,因此,自然法的要素在中国社会要比在欧洲社会更为重要。但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写成正式的法律条文,且其内容又以人和伦理为主,因此无法将其影响领域拓展到非人的自然。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像“一个至高存在”这样的观念虽然肯定从很早就有,但很快就失去了人格性,这些观念严重缺乏创世的想法,因此中国人不相信有一个天界立法者在创世之初给非人的自然颁布法律这样的观念。因此,中国人不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来破解或重新表述一个理性的至高存在所制定的法。当然,这并不妨碍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有巨大的科技发展。我们已经讨论了它的许多方面,不过其深远影响可能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产生出来。
p25
在现代科学看来,我认为自然法中已经没有了命令与义务的观念残余。自然法现在被视为统计上的规律性,只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或大小范围内有效,是描述(descriptions)而不是规定(pre-scriptions)。这里我们不敢贸然参与主观性在科学定律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争论,但的确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走西方科学实际所走的道路,我们能否认识到统计规律性及其数学表达呢?我们也许可以问,假如某种文化想产生开普勒式的人物,是否一定要有那种将产卵的公鸡依法起诉的心态呢?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Sam Wolf摄于 1968年,感谢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照片)
目录
导言 1
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4
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44
科学与社会变迁 111
4.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 142
5.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165
6.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176
7.时间与东方人 203
8.人法与自然法则 280
附:台译本序 312
===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